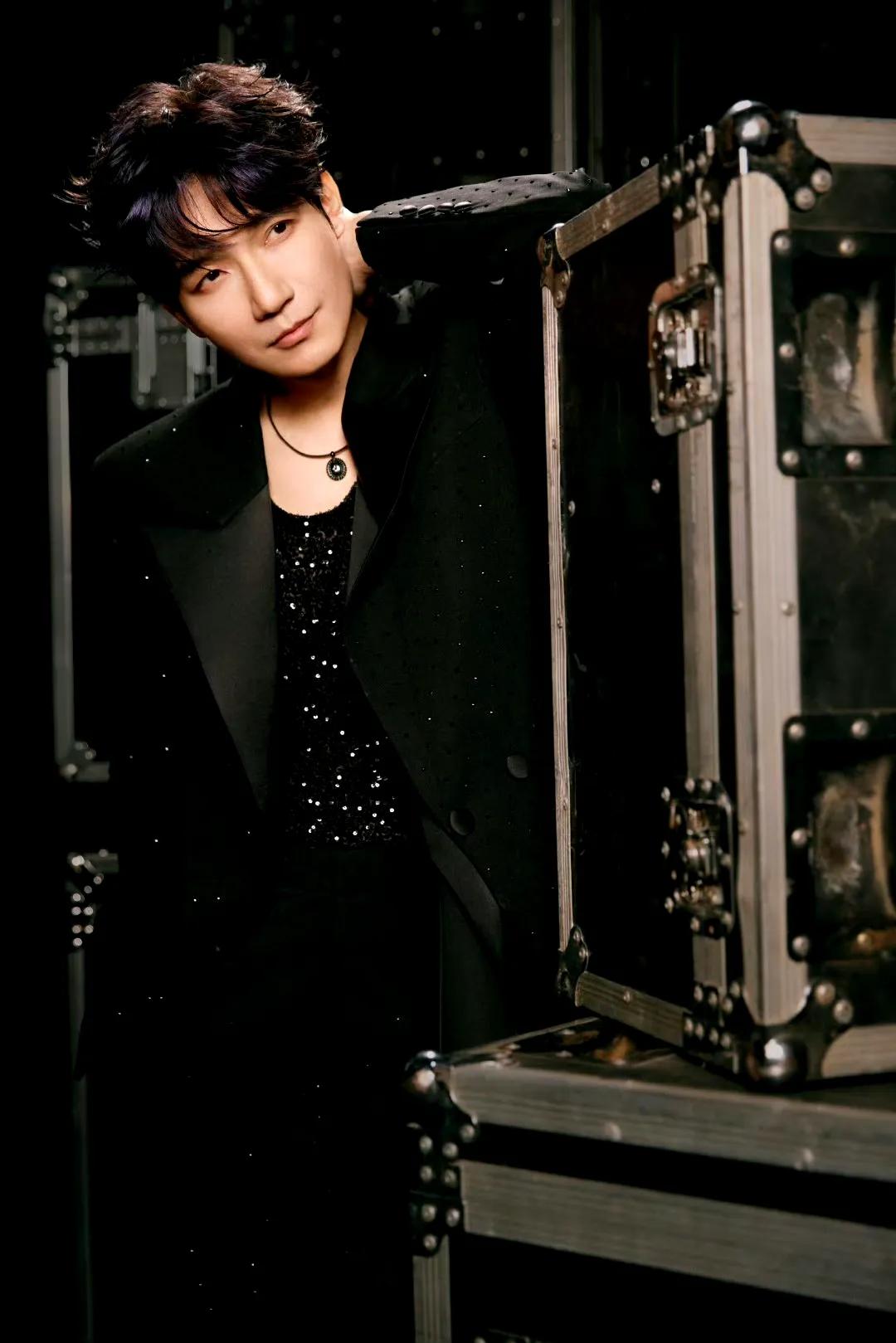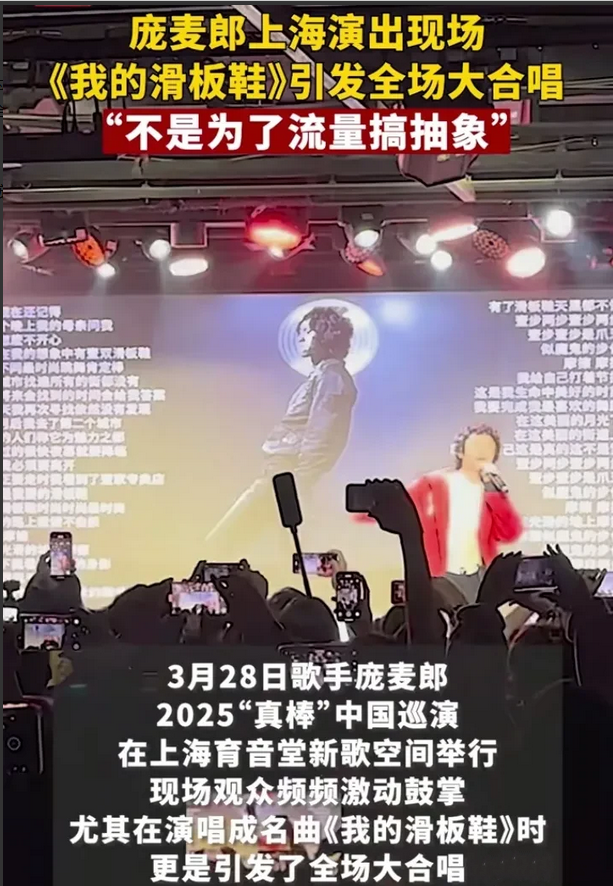于会泳的女儿于佳易生于1954年11月,从小在上海接受系统的音乐培训,后来考入歌舞团。
于会泳是一个深得人们敬重的大孝子,生活安定后,他便决定将母亲从山东乳山的乡村老家接到上海一同居住,以尽孝道。同时,他的妻子任珂也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人,作为家中长女,她负担着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尽全力支持着他们的教育。这些因素使得于会泳一家的经济状况时常感到拮据,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以坚韧的精神生活着。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中,于会泳是个典型的“怕老婆”的丈夫,许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任珂共同抚养了两个女儿。长女于佳易和次女于佳其从小便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养成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于佳易,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她从小便展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于佳易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歌手,1989年,她移居到了澳大利亚,继续从事歌唱艺术。虽然身居海外,她却始终未曾忘记自己的故土,仍多次回国,回到山东乳山老家探亲,传递着对家乡的思念与热爱。在家中浓厚的艺术氛围中,于佳易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即使年纪小,她也能在音乐会上安静地坐上好久,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每当父母准备去听音乐会时,她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和他们一起去,最终母亲常常会把自己的票让给她,让她有机会亲身体验音乐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音乐与艺术氛围的家庭里,于佳易和妹妹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热爱大自然与生活。每年春天,妈妈总会给她们姐妹俩穿上色彩鲜艳的绿色衣服,一起去公园感受春天的气息。妈妈和爸爸时常哼唱着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和鲁宾斯坦的《春之歌》:“春来了,春来了,她带着温暖,她含着微笑……”
2021年的悉尼华人跨年晚会上,一位优雅从容的女士坐在评委席上。她专注地聆听着台上选手的演唱,时而低头记录,时而微笑点头。这位评委正是华人音乐圈知名人士于佳易。作为一位资深音乐人,于佳易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源自她年少时期在上海的系统培训。
时光倒流至1954年的上海,初冬时节,于佳易诞生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她的父亲于会泳是当时文艺界的重要人物,家庭环境自然为她的音乐启蒙提供了得天独时的条件。在当时的上海,西方古典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交相辉映,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氛围为年幼的于佳易打开了艺术的大门。
从记事起,于佳易就生活在音乐的世界里。在上海的老房子里,钢琴声、小提琴声此起彼伏,这是当时很多艺术家庭的共同写照。上海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音乐影响的城市之一,拥有完备的音乐教育体系。于佳易得益于这样的环境,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声乐训练。她的音乐课程不仅包括声乐基础,还涵盖了乐理知识、视唱练耳等专业内容。
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于佳易最终如愿考入了歌舞团。这是她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歌舞团期间,她不仅要继续提高声乐水平,还需要掌握舞台表演技巧。歌舞团严格的训练制度和丰富的演出实践,让她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每一次排练和演出,都是对她专业素养的考验和提升。
于会泳在京剧音乐的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尤其是在唱腔创新方面。他的创新方式不同于许多前人的尝试,而是通过将地方戏曲和曲艺的腔调融入京剧,成功开创了新的唱腔形式。许多人都尝试过突破京剧的传统唱腔,但往往面临困难,不得其法。有些人拼命运用高八度音调,甚至有演员违背唱腔的自然走势,结果演出变得不自然。于会泳则通过分析多种地方戏和曲艺,汲取其音乐素材,并将这些元素与京剧的西皮、二黄融合,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表现力,使得其唱腔既新颖又不失传统韵味。
在八大样板戏公演后,特别是《杜鹃山》的乐曲和唱段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许多专家认为,《杜鹃山》的乐曲是八大样板戏中最美、最流畅的,至今也没有任何现代京剧能够超越它。于会泳对京剧的贡献,特别是在将管弦乐伴奏与京剧唱腔完美融合方面,推动了现代京剧的创新与发展。如今,当人们欣赏《杜鹃山》中的唱段时,特别是杨春霞演绎的部分,不禁为其深情与优美所打动。
而于佳易,作为于会泳的女儿,她曾是铁路文工团的一员,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向许多从未见过大歌舞团演出的铁路工人献上了自己的歌声。她演唱的歌曲,不仅包括大家熟知的流行歌曲,还特意选取了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其中《小木屋》便深深打动了工人们的心。那温柔而富有感情的歌声,诉说着工人们的艰苦与坚韧。当她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唱完毕时,工人们纷纷上前,拿出他们那已经磨损的日记本,伸出手请求她签名。她的歌声让他们感到无比温暖和振奋,仿佛给他们的艰苦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
于佳易的演出不仅仅是传递音乐的力量,也让那些长时间不能接触到艺术的工人们感受到了一种亲切与关怀。她通过歌曲讲述了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真切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每一次演出,工人们的反应都让她深受感动,也让她明白了音乐的真正力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