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一名苏联逃兵带9个日本女战俘逃往深山。此后,逃兵成了“皇帝”,10个人在山林中一直生活,19年后,逃兵有了73个孩子。
那是二战刚结束的日子,苏联红军打垮日本关东军,俘虏了六十多万战俘。勃日涅科夫是押送队的小兵,二十出头,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他奉命带一队女战俘去后方医院帮忙,车刚开出没多久,暴风雪就糊了路。
他眯着眼开车,雪花打得挡风玻璃咔咔响,视野模糊得像蒙了层纱。车轮一滑,轰的一声,地雷炸了,车斗里血腥味扑鼻,二十多个女人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九个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
他跳下车,腿抖得像筛子,脑子里全是回去挨罚的画面。他咬咬牙,拽起枪,指着她们挥手,吼着让她们下车。她们抖着身子,眼神空洞,跟着他跌跌撞撞跑进林子。
雪林深处,风像刀子割脸。他找了片背风的山坳,搭了个窝棚,用树枝和破布挡住洞口。九个女人挤在角落,衣服湿透,冻得牙关打颤。
他点起火,烤着手,盯着她们,眼里闪过一丝邪光。她们是日本护士和士兵家属,模样清秀,年纪从二十到三十不等。
他舔舔干裂的唇,脑子里转着歪主意。他拿枪比划,示意她们别动,自己捡了根木棍,在雪地里划圈,指手画脚让她们听话。她们不懂俄语,眼神惊恐,可没一个敢跑。他心里得意,觉得自己在这儿就是皇帝。
日子一天天过去,窝棚里烟熏火燎,空气里满是汗味和土腥。他用枪逼她们干活,自己拿着仅剩的几发子弹打猎,抓些野兔野鸡回来。她们不会打猎,就在窝棚边挖坑种菜,捡柴烧火。
他吃饱了就往她们身上扑,第一个反抗的女人被他一拳打晕,拖进角落,衣服撕得稀烂。她们哭着缩成一团,眼泪冻在脸上,可他不管,夜夜折腾。
没多久,女人肚子里有了动静,他咧嘴笑,觉得自己在这儿建了个王国。可这“王国”没他想的那么美,粮食不够,冬天冷得像冰窟,他瘦得皮包骨,眼窝深得像枯井。
几年过去,窝棚变了个样。树枝搭的棚子换成土坯房,周围多了几块菜地,女人用破布缝了衣裳,裹着一个个孩子。
十九年间,她们给他生了73个娃,大的十七八岁,小的还在襁褓里。勃日涅科夫从“皇帝”变成了苦力,白天扛着锄头挖地,晚上被她们拽进屋,累得喘不上气。孩子多得像窝兔子,哭声吵得他头疼,食物总不够,他打猎的手抖得拿不稳枪。
她们里头有几个懂医,能接生也能治病,娃娃们才没死光。可日子越过越苦,他脾气大了,动不动挥拳头,可女人不怕了,反过来拿棍子围着他打。他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眼里没了光。
这转变从哪来的?他开始时拿枪吓她们,可子弹早打光了,枪成了空壳子。
有天晚上,他睡得迷糊,一个女人趁机抢了枪,举起来砸他脑袋。他醒过来,脸肿得像猪头,枪被她们拆了扔进火堆。她们围着他,眼里冒火,拿绳子绑了他手脚,逼他干活。
他从“皇帝”成了奴隶,白天挖地种菜,晚上被她们折腾,日子像地狱。他想跑,可山里路太险,孩子越来越多,他跑不动了。她们守得紧,轮流看他,眼神冷得像冰。
他熬了十九年,胡子长得像野人,腿脚抖得站不稳,终于逮着个机会,趁她们睡熟,摸黑跑下山。
他跌跌撞撞跑到村口,敲开一户农家,蓬头垢面,像个疯子。主人吓得腿软,赶紧报警。警察来了,他喘着粗气,语无伦次地说自己是逃兵,带了九个女人躲山里,生了七十多个娃。
警察半信半疑,盯着他那张风霜刻满的脸,觉得像胡话。可他死拽着警察袖子,要带路。车开进山,雪地里踩出一条道,到了窝棚,警察傻了眼——九个女人,七十三个孩子,窝棚里挤得像蜂窝,个个衣衫褴褛,眼神野得像狼。
他站在旁边,低头不吭声,眼泪淌在胡子上。警察核实身份,查出他本该死了,名字还刻在烈士碑上。消息传开,苏联震怒,把他名字抹了,日本警方接手女人和孩子,把他们送回国。
法庭上,他低头认罪,逃兵罪加上私自扣留战俘,判了十二年。
他没喊冤,蹲进牢里,眼底反倒松了口气。
山风还在吹,窝棚空了,雪盖住了脚印,像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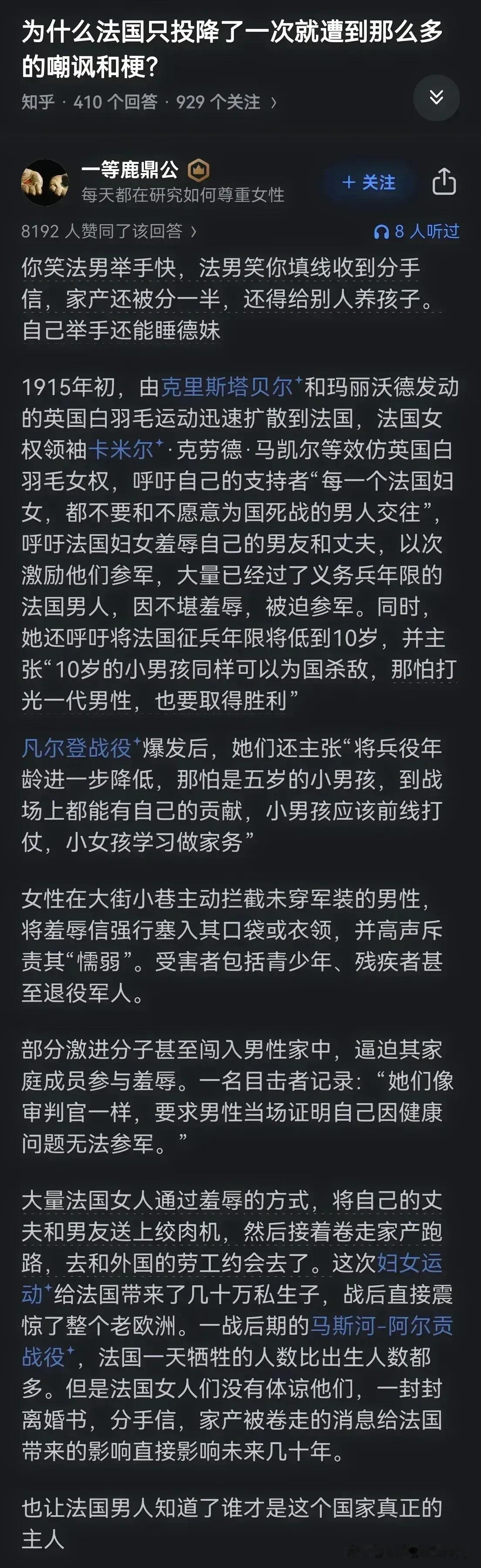






用户10xxx49
讲天书。鬼信你的谣言。进深山她们吃什么。装什么呢,那么多孩子吃山上水长大的。住那里呢。
敌杀死 回复 03-25 15:09
这个真有哦
我是传奇海狼
改变过了?🤔以前的男主是一个日本兵啊!
dm123_88
狗嘴里的故事!
艺海翰林
精彩的故事,希望它是真的!!
百汇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