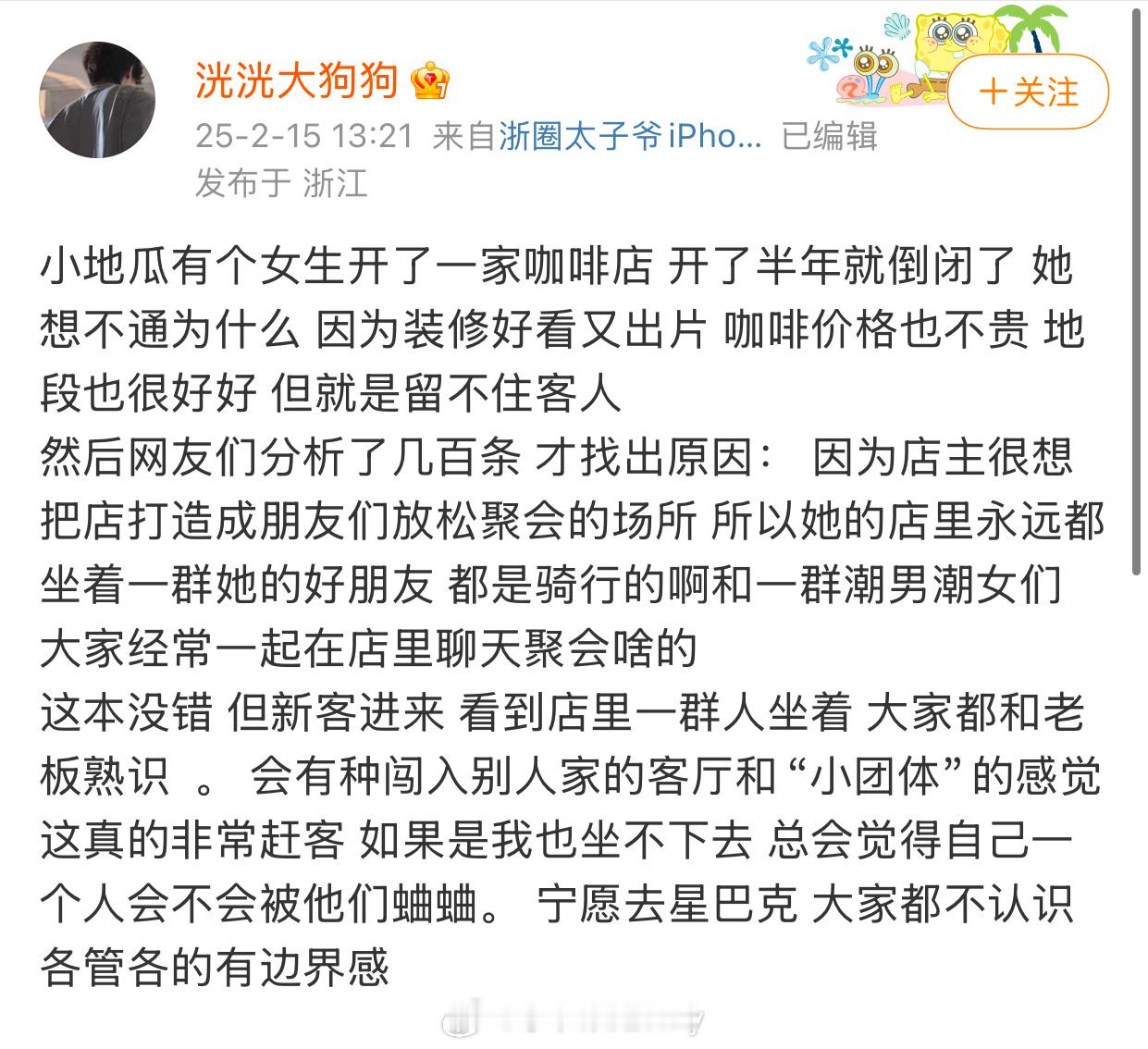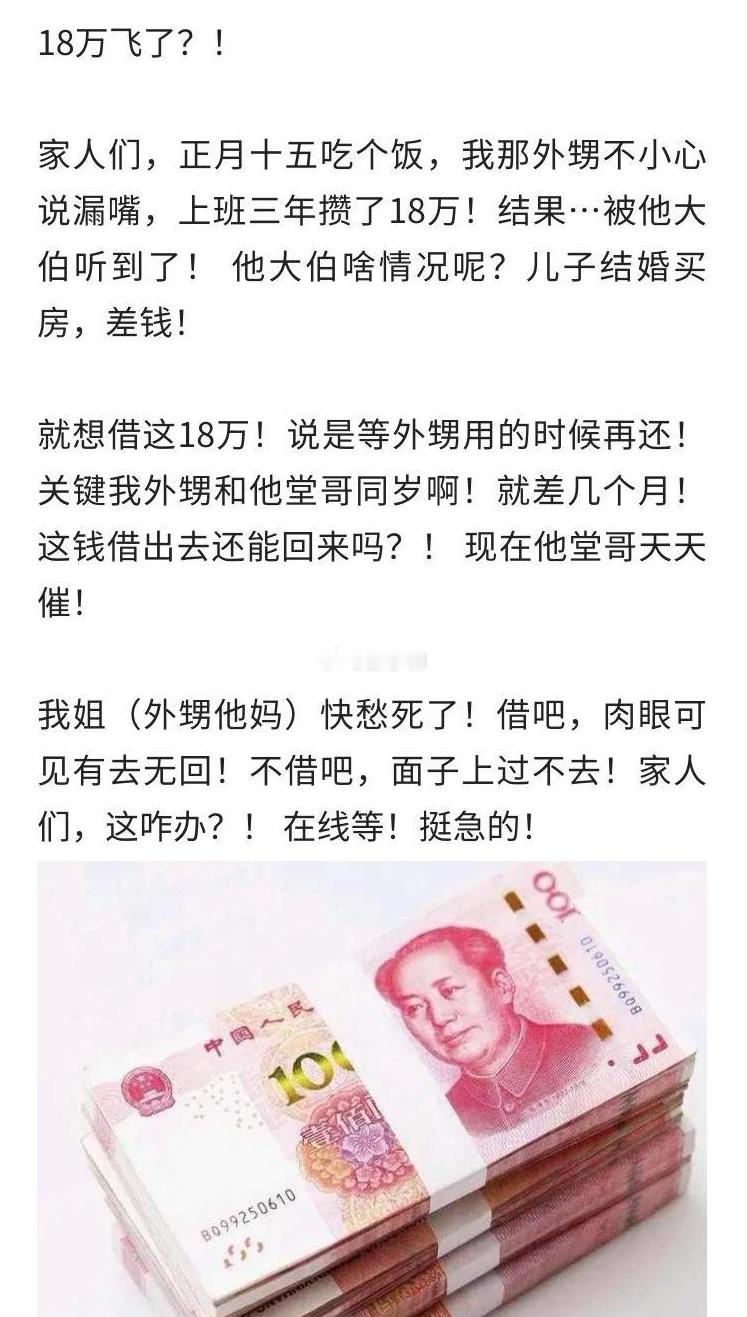辽河鱼趣之四一一提虾。 我一般不吃现在市场上又肥又大的虾,因为知道那绝大多数都不是野生的。几十年前的提虾经历,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纯天然的对虾,咱们这叫“虾驹子”。 辽河口大苇塘是由原来的沼泽地改造后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沟渠坑塘是鱼鳖虾蟹的天然牧场。这里可以下地笼子提海鲇鱼,可以下挂网,但必须是悄悄地进塘。因为辽滨苇场为了保护苇子有一支看塘队,十几个老头穿短衣带草帽骑自行车,天天巡视这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看到下网的就抓,或没收或当场踩个稀烂。 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那么大的苇塘进去百十人就像豆子掉进河里一样。芦苇这东西非常韧,轻易踩不死、拔不动、撅不断。 孩子们正兴高采烈地打鱼摸虾,一声“看塘的来了!”,但见远处坝上一溜自行车鱼惯而来,好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夜袭队”。大家马上藏起网具躲起来,也有胆大的游到沟对岸扯着嗓子唱:“星期天的早晨白茫茫,看塘的老头大裤裆,李金手一挥,一起往前追。” 李金是队长,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一副黑脸,得罪了不少人,苇塘闸门上就有一些用瓦斯灯烧上的骂人话,那些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书归正传,提虾用的是一根弹性钢丝做的网圈,盘起来挂在自行车上就走,放开有一张八人桌大,一根粗竹竿加六根网纲提起来。一般选在沟塘边水深一米左右的地方,沉下网后保持网纲在起来前纹丝不动,这需要一份定力。因为虾驹子前面的两条飘飘悠悠的长须非常敏感,水中稍有波动它就立即弹跳出几米,这是自保的基本功。 一般来说,如果选的地方差不多,三两网能上一只虾驹子,个别有一网三四只的时侯,但很少见。 静待它们上网时,可以欣赏周围的景色:小梭鱼咬着水面上倾倒的芦苇玩耍,骚夹子鬼头鬼脑地钻出来,看见人后马上又躲进去,苇喳子(一种水鸟,习惯用茎草缠在三根芦苇上做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海鸥时不时俯冲下来沾水即走,长脖老等能从你下网到收工都站在蒲草中一动不动,灰突突的鹌鹑领着一群小崽从红碱蓬棵子里一闪而过,这是如今的孩子们再也看不到的画面了。 一天傍晚,我和父亲在市区通向西炮台矿渣路上一条南北走向的沟里提虾,这里有两根水泥管连通公路两旁,无意中形成了小范围流动性,引来了逐水而行的虾驹子们。三个小时里,共提了五斤多虾驹子,记得煮了满满一盆红亮诱人。代价是,浑身上下被蚊子咬了无数大包,这就是地方好有货提,为什么没有人去的原因。 奇怪的是,晚上十点后起了风,蚊子少了,虾也提不上来了。什么原因,到现在也搞不明白。 冬天时我用干虾驹子加酸菜心做汤款待同学,金黄的菜心配上红白相间的干虾,点上几棵翠绿的香菜十分诱人,一会功夫就见了盆底。 我想再做一份,一个同学醉熏熏地指着剩下的虾说,就用开水沏上,这鲜味足够了。 现在想一想,自然生长在苇塘的虾,一生中既要追逐浮游生物又要躲避天敌,浑身肌肉弹性十足,其鲜美口感是靠人工喂养的虾根本无法相比的。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速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