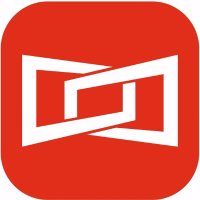记者闫桂花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Goldin)的最新研究显示,大多数补贴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恐怕还远不足以显著提升生育率,因为没有触及到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将社会从以传统为主的、较孤立的和农村化的状态迅速推向现代化,导致剧烈的代际和性别冲突,带动生育率急剧下降。
她在去年12月发表的最新论文“BabiesandMacroeconomy”中指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结合社会政策和文化变革,特别是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和生育过程中的性别冲突,对此,美化父亲角色,或许是一个好的起点。2023年,戈尔丁因性别差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生育率低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无论是在欧洲、北美还是亚洲许多国家,生育率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下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之下。在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每位女性一生平均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得下一代人数能够替代当前的人口规模。
不过,即便在这些生育率下降的国家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戈尔丁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过去近百年经济增长相对持续稳定的国家,代表是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美国六国,在这些国家,生育率虽然下降,但降幅比较平坦;另一组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非常大,尤其是二战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生育率波动也较大,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3左右的超低水平,这类国家以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六国为代表。
为何经济增速快的国家生育率反而急剧下降?戈尔丁的研究指出,剧烈的经济变化让女性受益更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也极大增加,与此同时,工作和生育的平衡也就更加必要。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没有给观念的变迁留下足够的时间,尤其是,男性的观念变化相对女性较慢,从而带来了剧烈的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
她进一步指出,第二组国家大多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比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而韩国和日本则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些文化和传统中,男性通常会被赋予更多的权威和主导地位,包括家庭决策和经济支配权,继承土地和家族事业等,这种观念强化了男性对传统的依附,也让他们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社会规范。
戈尔丁的模型也显示,男性从父权制中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传统,而女性则希望通过现代化获得更多平等。面对剧烈的代际矛盾、性别分工的不统一,尤其是男性的“适应断裂”,女性倾向于选择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在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上也无法与男性同步。
相比之下,在第一组国家里,因为经济发展是个持续缓慢的过程,代际观念的转变也一直在平稳进行,体现在生育率上,即便下降,速度也相对平稳。
戈尔丁援引的数据显示,在第二组国家,女性每天从事的无收入劳动比男性多出3小时以上,相比之下,在第一组国家,家务和育儿责任在性别间的分配更加均衡,例如瑞典和丹麦的性别差异仅为0.8-0.9个小时。

从下图可见,第一组国家在20世纪初的总和生育率普遍低于第二组,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波生育率反弹小高峰,此后稳定在1.5-2之间。第二组国家最初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较高,但下降速度很快,最近三四十年几乎一致徘徊在1.5左右,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二战以来一路下跌,目前已经降至1以下。

此外,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场所也从农田走向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工厂和服务业部门,这种迁移对解释生育率的变化非常重要。戈尔丁在论文中指出,通常来说,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拥有更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更坚守传统的做法,第一代移民的儿子们确实如此,但女儿们则从现代化的生活中获得了更多选择和自由,冲突由此产生。
第二组国家普遍经历了更剧烈的城镇化过程,其城镇化过程对生育率的影响也更大。戈尔丁指出,1960年,日本农村人口占比为37%,是第二组六个国家里最低的,但仍比第一组国家中农村人口占比最高的美国高出7个百分点。到2023年,第一组国家平均农村人口占比降到了16%;第二组降至21%,其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2000年代早期。
“快速的经济变革往往会挑战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信念的改变比技术和经济的变革要慢得多。传统的人们常常被突然推入现代化的社会,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信念、传统和社会习俗。因此,迅速的经济变革可能引发代际和性别冲突,并迅速降低出生率。”戈尔丁在论文中称。
生育率下降往往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继而导致消费低迷、创新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并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延缓这一过程,包括现金补贴、育儿和教育补贴、延长产假等。
迄今为止,东亚国家采取的这些政策收效甚微。比如,日本每年向18岁以下儿童提供每月1万到1.5万日元的补助,并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额外补贴,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生育率仍在持续下滑。
相比之下,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采取的类似政策效果较为明显。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MtthiasDoepke在2022年发表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在欧洲等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生育率现象:人均GDP越高,生育率越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高。Doepke认为,背后原因主要有四个,包括有效的家庭政策——产假、育儿支持等;合作的父亲——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职责;以及,良好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戈尔丁认为,国家之间确实出现了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在单一国家内部,普遍的趋势仍然是,生育率随经济发展逐步下降。一个特例可能是美国的“婴儿潮”时期。从1946年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出生率急剧上升,而在这之前或之后,总和生育率都相对较低。
“这一时期的生育率部分是通过美化婚姻、母亲角色、‘贤妻’和家庭实现的。那么,今天是否可以通过美化为人父母,尤其是父亲的角色,以及改变工作场所规则(如让父亲在请假和申请弹性工作安排时不受到惩罚)来实现生育率的回升呢?有一点是明确的:除非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以扭转,否则出生率可能不会提高。”戈尔丁说。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提高生育率刻不容缓已成为共识,相关政策也已陆续开展,但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依然停留在如何帮助女性应对职场和家庭平衡上面,远未触及戈尔丁所说的“性别冲突”和“代际冲突”层面。真正能提升生育率的政策要具备哪些特点?戈尔丁的这份研究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让男性承担更多家务,以及美化父亲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