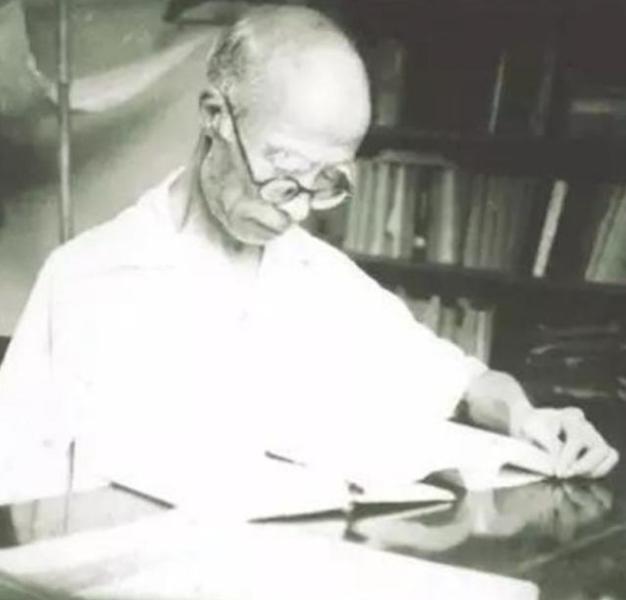1942年8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宓,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每个领域只选1人,全国只有16人入选。让吴宓感到欣慰的是,当年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和他本人,同时位列其中。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吴宓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抗战胜利后,因为对胡适一派的深恶痛绝,吴宓没有北上,而是留在了大西南。 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说,这是虎落平川。 1949年,对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究竟是北归还是南渡? 这是一个问题。 吴宓天生优柔寡断,当时,他是有机会南渡的。1948年,美国的大学曾请他赴美讲学,1949年,香港大学和钱穆都曾向他发出邀请函,远在台湾的傅斯年也曾力劝他赴台,但吴宓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他说,世事沧桑巨变,不如隐去,化作剑南人,找个清净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遗憾的是,时代的狂潮淹没了他的愿望。 吴宓的悲剧,起始于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 这一年,吴宓在课堂上讲解“犹况”的句式用法,一时兴起,说了一句,“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潜伏在课堂上的“积极分子”,认为这是对大饥荒的讽刺,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恶毒攻击。 就这样,吴宓被当作“白旗”拔掉了,从此失去了为学生开课的资格。 处在战栗与痛苦的境况里,吴宓极为牵挂同病相怜的老友陈寅恪。1961年,经过长途跋涉,吴宓终于在广州见到了陈寅恪,那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五天。临别时,陈寅恪写了四首《赠吴雨僧》,其中两句,竟一语成谶,“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从广州回来后,吴宓发现,天空已经黑云密布,脚下再不是清净的校园,而是陷阱和地狱。 风暴来的不是慢,而是让人窒息的宏大。 1966年,吴宓作为“牛鬼神蛇”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毒打,罪证竟然是他直行书写,写繁体字。 关在小黑屋里,吴宓的左腿骨折了,没有吃的,疼痛与饥饿让他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一边拍打上锁的木门,一边发出哀婉凄厉的呐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 如此被侮辱与被伤害,深深地刻在了吴宓的骨头上,神经里。 这是比疯掉更痛苦的折磨。 1972年,被摧残的既瞎又瘸的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里。自1970年起,吴宓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了,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买药,看病,请老婆婆照看生活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内。因为不够用,吴宓不得不靠借债度日。 那一时期,他写给老友的信让人心碎,今恳求兄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 往事不堪回首,曾几何时,吴宓是那样的仁善,别人来借钱,他总是借给,之后却很少要回来。现在,他已经穷困到无钱度日的地步,却不提还钱,而是要借。 其实,学校欠他的工资已经有1万元之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有人打听到,如有特别需要,吴宓可打报告从被扣的工资中支取少部分,于是纷纷来找吴宓谈话。 如果你认为这是人性的善,那就太天真了。 这些人来找吴宓谈话,只有一个目的,以借的名义榨他的工资,如果不从,就用更残酷的手段来整他。 人性恶的阀门被这样打开后,那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近乎成了最悲惨的世界。 当得知吴宓可以支取被扣的工资后,有人开始偷他的书,然后要求他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去,等赎完了,再全部偷出来,要他再赎一遍。 更有甚者,知道吴宓好善乐施,竟直接拿一张白纸来,声称这是一位同学的来信,急需一笔款子住院动手术,请吴老师帮忙。 1973年9月,吴宓老家的妹妹吴须曼来重庆看望哥哥,当走进那间小黑屋时,顿时泪如雨下。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了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一张,哥哥剩下的家当只有一只小皮箱,一条破被子还有一顶购于1938年满是窟窿的蚊帐。 见此情景,吴须曼扶着哥哥到学院储蓄所想取一些钱出来,结果营业员告诉吴须曼,吴宓1万元的工资已经全部被取完了。 吴须曼问哥哥,1万元的工资,怎么就没有了? 吴宓断断续续地说,都借出去了。 完了,还要加一句,济人之难总是好事。 吴须曼听了,想找那些恶毒的人理论,但走出几步后,终究还是放弃了。 因为恶毒的人头颅扬的那么高,手里还持有红色的鞭子。 吴须曼见哥哥老无所依,朝不保夕,想把吴宓接回老家,但吴宓却不愿回去。 起初,吴须曼感到困惑,后来才知道,有人为了能够持续不断地榨取吴宓的工资,便绘声绘色地恐吓他,说回到老家就没有人保护他了,夜里更会有劫匪来害他。 那时候的吴宓,已完全被恐惧吞噬,他不怕死,但惧怕人间的鬼。 1976年,太阳终于重新升起,吴须曼来接哥哥回家,当吴宓捧出枕下仅剩的七分钱硬币时,吴须曼哀伤不已。 回到陕西老家,吴宓多活了一年,1978年1月,在孤独与惊惧中,吴宓凄惨死去。 临终之夜,他在黑梦中惊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