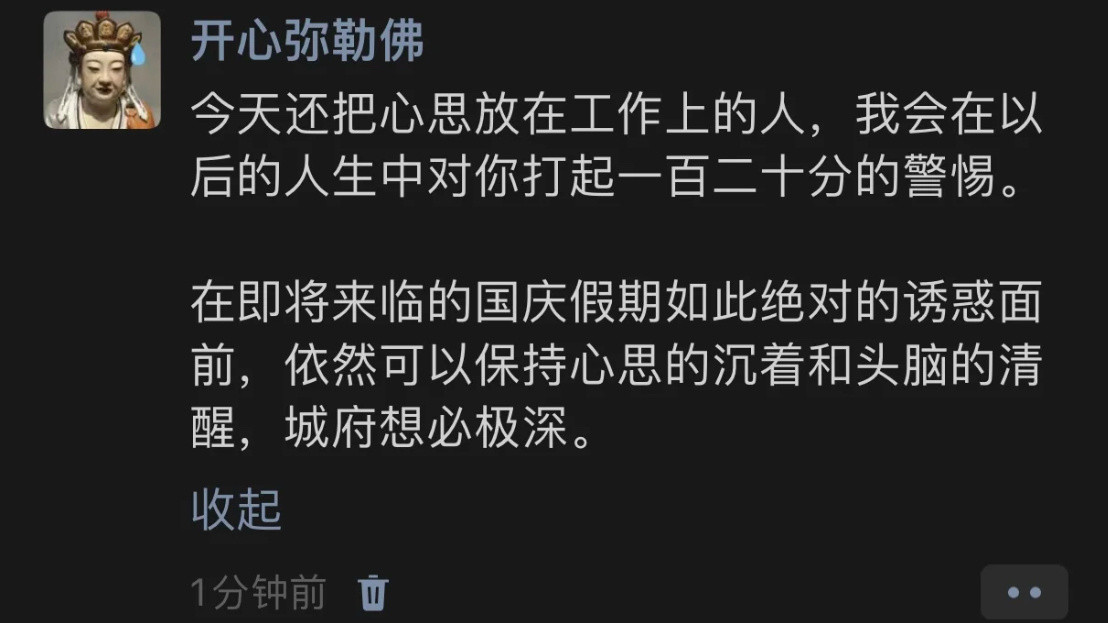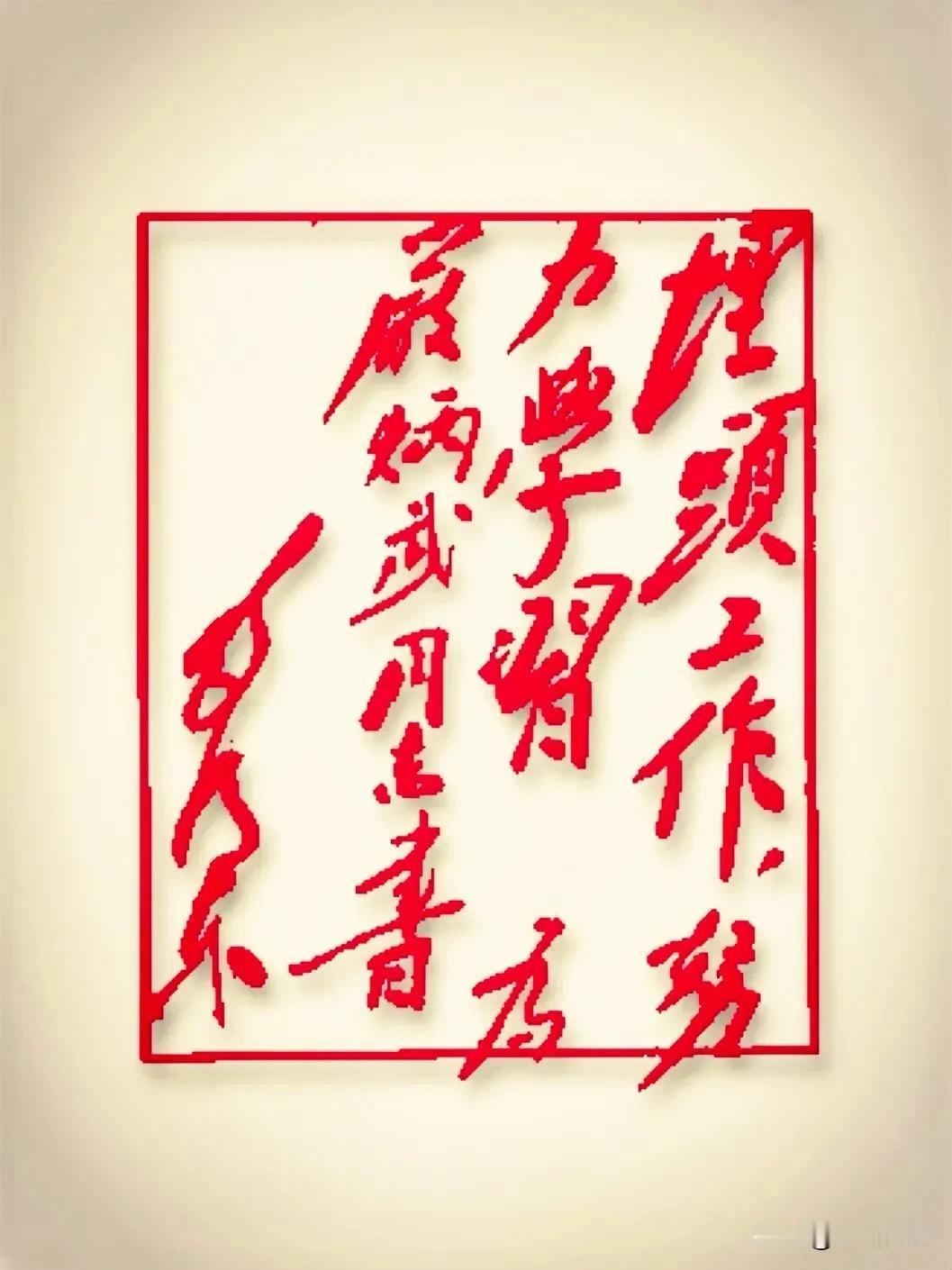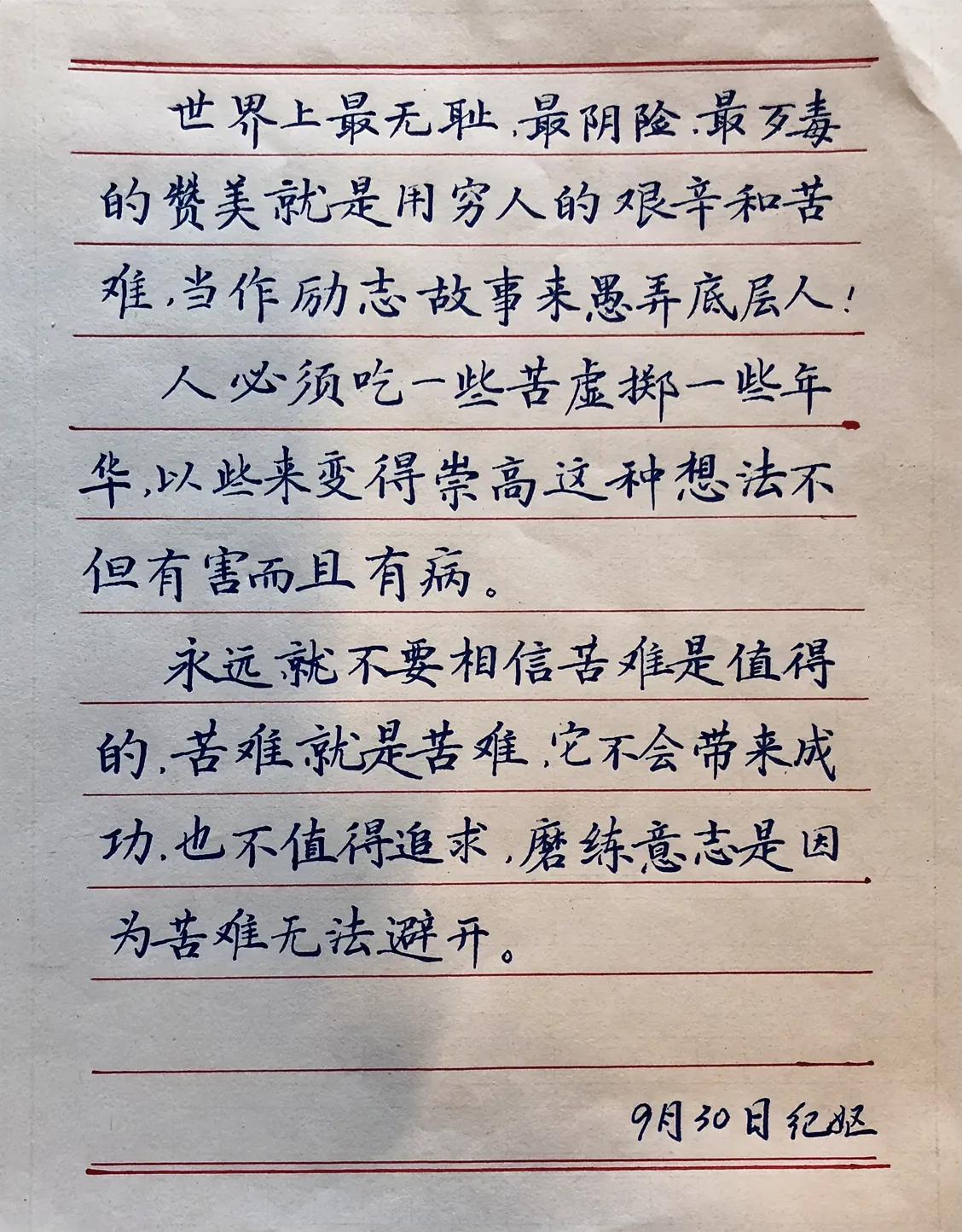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暴露黑暗,解释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解释恶的成分。莫言小说的语言独具匠心,展现了两个鲜明的特色:“喋喋不休”与“胡言乱语”。“喋喋不休”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雅俗共赏、泥沙俱下的特质上,还通过大段细腻入微的瞬间感觉描写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胡言乱语”则巧妙地展现在语言词汇的变异创新和大量别出心裁修辞手法的运用上。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从莫言小说中那些滔滔不绝又看似“语无伦次”的语言里,我们可以窥见他那喷涌而出的强大想象力,如江水绵绵不绝。 莫言的小说叙述风格被冠以“莫言叙述”,主要体现在多样化的叙述视角和众语喧哗的叙述风格两大方面。首先,叙事视角灵活多变,第一人称的运用花样百出,第二人称则引发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复合式人称视角自如转换,以及自然流露的儿童视角,使得小说叙述不落俗套,充满张力。其次,小说中的叙述者摆脱了作者的专制统治,各种声音和意识平等地各抒己见、自由诉说,不同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众语喧哗、多音齐鸣的叙述风格。这种不拘一格的叙事视角和独具特色的叙述风格,正是莫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小说叙述上的生动体现。 在莫言的小说中,想象的碎片俯拾皆是,它们如同璀璨星辰,点缀着文本的夜空。以《金发婴儿》为例,莫言通过瞎老太婆这一形象,将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她摸着被面上略略凸起的图案,龙凤仿佛在她的手下获得了生命,嘶鸣着、飞舞着,将她的身体都掩埋在了金色的羽毛和绿色的鳞片之中。这幅游龙戏凤的画面,需要超人的想象力才能构建。龙凤呈祥的被面本是平面的,但在想象的加持下,它们变得立体而生动,嘶鸣着、翻飞着,为瞎老太婆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而龙凤这些远在天边的神物,也在想象的阶梯下,变得触手可及,甚至成为了遮身御寒之物。一个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是无法描绘出这样辉煌壮丽的景象的。 莫言的小说中,名字也往往富有深意。如《蛙》中的主人公“蝌蚪”,这一名字便蕴含着深意。蝌蚪是青蛙的生命之始,其成长过程与人类生命的孕育过程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蝌蚪的形状与人类的精子相似,而变态发育期内的蛙,其形态又与三个月大的婴儿相似,都拖着尾巴。而“蛙”与“娃”在民间更是同音,婴儿刚出生时的啼哭声与蛙的叫声也极其相似。在民间,“蛙”更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许多民间艺术都带有蛙的图案,因为蛙在远古时代就被赋予了多子多育、生生不息的深意。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即便是食的极度匮乏,也能激发人对饥饿的极端幻想式解决。《铁孩》中,饥饿年代里,一个叫狗剩的小孩看到铁孩把铁筋伸到嘴里咬着吃,于是也开始吃铁。他们如精灵般穿梭于废铁堆中,吃铁、吃铁轨,甚至把追捕他们的射手的枪也抢来吃了。这种对饥饿的“幻想”式表达,背后藏着的是另一番真实。 莫言以自身经历为蓝本,描述了1961年春天,村子里的人们因极度饥饿而吃煤的情景。这种吃煤、吃铁与吃美食的快感完全一样的描述,既包含了深深的无奈,也蕴涵着一种生存的机智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作家对现实苦难的超越,也是中国乡村艺术中幻想式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生动体现。 莫言的小说还大量运用了民间语言的口语化、俗语化表达,如村言俚语、顺口溜等。这些质朴无华的体裁,表现了老百姓对生活切身的体验,平实中透露出一种诙谐与睿智。莫言的小说汇融了这些民间艺术,不仅语言鲜活生动,而且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小说《幽默与趣味》则形象地隐喻了生于农村的城市人的痛苦。大学教师王三生活在文明的城市里,但却对这种文明感到压抑和恐惧。他被五颜六色的车子逼得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感到自己被文明挤瘪、压垮了。周围的人群冷漠无情,警察野蛮凶狠,售货员恶声恶气,老婆粗鲁蛮横。王三无法融入这个环境,多年来一直战战兢兢地活着。他虽然幻想着苏北原野上的悠闲景象,但那也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当现实的灾难来临时,他只能变成一只猴子来逃避。 成为中国女性苦难化身的非《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莫属。忍受饥饿病痛是上官鲁氏的痛苦之一。作品中多次描绘了她因饥饿劳苦而变得浮肿、惨白或透明的脸庞以及肿胀的腿和酸痛的骨节。为了能喝上腊八粥,她带着年幼的儿女毅然加入了去县城的大军。但这条路对这些饥饿的人而言无异于长征的路途,充满了艰难困苦。 然而,这次长途跋涉换来的腊八粥并不能改变上官一家的根本困境。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她的女儿们不得不卖身或被卖走。解放后的饥荒年代,母亲更是被饥饿逼得只能用自己的胃来运粮养活儿女。而因封建思想带来的生育的痛苦、被歧视被打骂不被当做人、被迫与不同的男人生子则是她痛苦之二。莫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上官鲁氏的苦难人生,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历史进程中所承受的深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