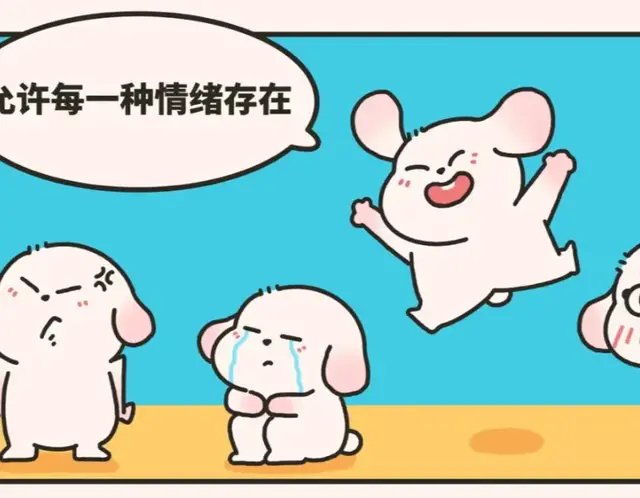全金陵城的人都知道,乌衣巷旁林隐堂里自封堂主的那位,出身名门,世代簪缨,连随便开个药堂都有皇帝老子御笔题匾,完完全全一个贵游子弟,整个京城没有谁能让他放在眼里。
除了一个人。林隐堂的少堂主。
虽然前面加了一个“少”字,但听闻那少堂主也只是比那堂主林跃本小了两岁而已。都说是一物降一物,林跃本平日里逍遥自在惯了,他若不高兴,谁的面子都不给,谁的场子都敢砸。可唯独对那少堂主是百依百顺,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甩脸子。
但这也只是听堂里做事的那些人私下提及,便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变成了坊间趣事,四处流传。
而实际上,那少堂主到底是何许人,到底长的什么模样任谁也说不上来。
只知那少堂主的医术极高且行事极秘,就连偶尔为王公贵族出诊,也是面覆薄纱,不露真容。有人甚至怀疑“他”根本就是个女人,什么“少堂主”的称谓不过是林跃本金屋藏娇不愿示人,故意伪造出的假象罢了。
然而猜测归根到底也只是猜测,真相究竟为何没有人敢断言。所以这件事渐渐被京中百姓归类成了京城第四大未解之谜。
但是说句实话,林跃本为人随性是随性了些,不过他那医术倒确实不是吹的。京中百姓有个什么大毛小病,头疼脑热的都爱跑去找他看看。他也从来不会用两副面孔对人。无论来的是朝中清贵,还是乞丐平民一律一视同仁。该排队的排队,该付钱的付钱。付不起钱的就暂时一笔一笔赊着,等还得起了再来还。因此,林隐堂在百姓之间口碑极好,当之无愧是金陵第一大药堂。
近来晋国与西楚战火刚熄,京中忽又爆发瘟疫。林隐堂里这几日天天都是人头攒动,里里外外被前来求医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林跃本和堂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夫一同坐镇,从五更忙到日暮,一刻也没歇过。待到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已是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四脚朝天躺在地板上,透过大敞着门望着天边的一处火烧云发呆,没一会儿眼皮渐沉,脑子便有些迷迷糊糊的了。
这时,正在外面扫洒的堂中护卫水宿心不在焉的挥舞扫把间一抬头,只见大门外飘然进来一人。那人一身黑衣,斗笠垂纱,一张脸藏在飘浮的面纱之后若隐若现,看不分明。然而那身形却似有几分熟悉。水宿下意识心中一喜,道:“承璐大哥?”
那人闻声却只字未应,默然又向前挪动了几步。然而他步子一挪水宿便觉出了异样,顿时警觉起来,手悄悄按上剑柄,质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抬手撩起那层黑纱,道:“是我。”随即目光绕过水宿,看向他身后躺在地上的林跃本,扬声道:“我要见堂主。”
水宿见他果然不是周承璐,心下一阵空虚。闷闷传话:“卖药的,听见没?有人要见你。”
林跃本眼睛也不睁,翻了个身懒懒一句:“不见不见。今天打烊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那人走近几步,到林跃本身前。
“是我也不见吗?”
“是天王老子也不见……欸?卫存?”
林跃本随即一骨碌坐了起来:“你怎么来了?”
卫存一笑:“我怎么来了?当然是因为你交给我的事情我都办妥了,来跟你讨赏来了。”
林跃本随手扔了一个软垫过去,卫存摘了斗笠顺势坐下。道:“这次我回来是以回乡丁忧为由,路过金陵,不能久留。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并州的事情,我想堂主应该已经听说了吧?穆尔卫现在正为此事恼火。他这个跟头栽得勾大,御史台的那帮人这几日想来也不会闲着。如此看来,情况正向着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
卫存顿了顿,压低声音:“如果要安排少堂主过去的话,这几日是最好的时机。如果不趁现在见缝插针,错过了,再想找机会可就难了。”
林跃本垂眸沉吟,眉头微蹙:“那边所有的布置都停当了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卫存说着话锋一转:“现在的时机虽然最好,但也会最危险的时候……少主还是心意不改,明知是虎穴狼窝,也非闯不可吗?”
林跃本无奈摇头:“你知道的。倔驴一头,一意孤行。侯爷都拦他不住我能拿他有什么办法?”
卫存叹了口气:“既然如此,便只能提醒少主多加小心了。我到时在朝中也会暗中照应,但凡事还是谨慎为宜。”言罢警惕的向外面望了望:“堂主,要说的就是这么多。凭虚阁的探子最近盯得很紧。我不能在这儿待得太久,以防生变。”
转而音调一扬:“林堂主,外面都传你医术高明,我今日可是慕名而来啊。我肚子都疼了三天了,你不能就说几句话,连方子都不给写一个就开始赶人吧?医者父母心啊,你这样也太没有良心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小心我去京兆府衙去告你一状,让你这药堂开不下去!”
林跃本亦半真半假配合道:“去去去,你就告我去吧,反正这几天都累得半死,这药堂我早就不想开了。”半推半就间真把卫存给“轰”了出去,倒是像极了林跃本一贯的做派。
林跃本见水宿站在一旁看戏偷笑,没好气的朝他挥了挥手:“别愣着傻笑了,还不赶紧去准备车马?……明晚就送那头“倔驴”出京。”
秋风萧瑟,霜寒渐起。此时已是夜半三更。
林跃本独自一人候在林隐堂外的马车旁,时不时往宅子虚掩的大门中望去,神色似是有些不安。
月光之下隐约可见一只玲珑的银制蝙蝠趴伏在他耳廓,泛着蓝色幽光。
这时,宅中突然传出些许声响,门随即被悄悄推了开来。只见门后,一人玄衣玉冠,唇角噙着几分淡笑。身后还跟着一个青衣小少年。
林跃本见状迎上前叹道:“唉,你可算好了,你再不出来我这马都要闹情绪了。你看这蹄子蹶的。这是想把你踹飞啊……”
那玄衣人失笑:“我看是你想把我踹飞吧……”
“怎么可能?我可比它有耐心多了……”
林跃本笑了笑,转而一正颜色:“……靳潜,那边都替你安排好了。不过此行凶险,记住凡是量力而行。如果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一定让水宿传信给我,知道吗?”
“放心吧林大堂主,我有分寸。”
“你有分寸,你能有什么分寸?若不是我这里实在脱不开身,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你一个人去冒险的。”
然而这边话音刚落,便听站一旁的水宿一脸嫌弃道:
“你真是啰嗦,不是有我在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林跃本眉头一扬:
“有靳潜在你身边胆子大了是吧?我再啰嗦也没你啰嗦,就是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靳潜好静,你别到时候啰里啰嗦把他烦死了误了大事。”
“哼!臭卖药的,嫌我不行你来啊”
“我来就我来,我……”
“……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会儿?要不要去那边打一架?”
白靳潜虽早已看惯了这两人互看不爽多年,但是对于两人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还是很难忍受,要是不叫停他们就能这样无聊的吵上一个时辰。
水宿是友人岳清宵安排过来协助自己的,照理说岳清宵那么闷的一个人身边怎么会有一个那么能说的手下,还有林跃本,严格来说也是岳清宵的人。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互补?
被这么一调停,两人这才心有不甘的停止了斗嘴。
白靳潜随即拍了拍林跃本的肩头道:“我走了。”
林跃本神色少有的肃然,认真点了点头:“各自珍重。”
水宿也跟着白靳潜上了马车,临行还不忘朝林跃本做了一个鬼脸。林跃本亦不甘示弱,一个大白眼回瞪回去:“臭小子,看回头我怎么收拾你。”
马车在长满了苔藓的青石板路上摇摇晃晃,很快便驶出了晋都金陵。北上向秦国国都长安驶去。
旅途乏闷,晃得人昏昏欲睡,水宿从行囊中拿出一个食盒,里面有他亲手做的梅花糕和糖酥饼,一打开食盒一股淡淡的糯米甜香便立刻扑鼻而来。
白靳潜一看见甜食,顿时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水宿最擅长做甜食,特别是他做的梅花糕,甜而不腻,细滑软糯,只要吃过一次就会觉得金陵城中所有糕点铺子的梅花糕一下子都黯然失色了。
白靳潜一边吃着边随口道:“水宿,你的手艺也太好了,这些东西都是谁教你做的?”
“都是侯爷教的,他知道少主爱吃甜的,所以教了我很多甜食的做法。”
“清宵教的?……他还会做点心?!”
“那当然了!侯爷会做的东西可多了,他平时不做那是因为他懒。”
“……”
白靳潜端详着手中白软的梅花糕喃喃道:“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他还有这一手,下次见面非让他给我做个十盒八盒不可……”
“岂止十盒八盒,只要少主想吃,就是七十盒八十盒侯爷肯定都愿意做。”
白靳潜闻言一笑:“我可没那么能吃,要真那样还不得把你家侯爷给吃穷了?”
两人说着同时笑了起来。然而笑着笑着,水宿的脸却慢慢阴沉了下去两眼盯着手中的糕点出神,发愣了许久才道:
“少主,你说……承琭哥哥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都出去这么久了,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办这么久的?我都问了卖药的好多次了,可是卖药的每次都说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就会回来,可是到现在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承琭哥哥他会不会……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白靳潜闻言一愣,没想到他会突然提起这件事,一时间有些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将手中剩下的点心一股脑全塞进嘴巴里,假装吃东西来争取一点思考的时间。
片刻,没底气道:“应……应该不会有事的吧,这次的事有些复杂,所以处理起来确实比平时要多费些时间……”
这个依旧含糊不清的回答完全在意料之中,水宿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默然半晌:
“那……至少等我们下次回金陵的时候应该就能见到他了吧?”
“嗯……嗯应该吧……”
白靳潜看着水宿失落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却又无从安慰。
一路无话,两人各怀心事望着沿途的风景发呆。
也不知这样晃晃荡荡了多少天,直到一天夜里,白靳潜迷迷糊糊之间感觉有人在拉自己的胳膊,恍惚间睁开眼一看,身边却一个人也没有。
白靳潜觉得奇怪忙掀开车帘,顿时被车外的景象怔住,只见前方不远处的长街上人流如织,灯火辉煌,一片繁华光景。水宿此时正立在车外,晚风轻拂起他鬓角的碎发,见白靳潜探头出来,对他微微一笑道:
“少主,长安到了。”
虽说如今的世道战乱连年,各地狼烟烽火一刻未息,但在长安的街巷中却闻不到丝毫战火的戾气,反倒是一派升平景象。
白靳潜和水宿找了一处客栈,好好的睡了一宿,把这几日没睡好的觉全都补上,直睡到日上三竿才依依不舍的告别床榻,下楼让伙计上了几样小菜。
长安的饭食不似金陵,白靳潜吃不大习惯,只草草吃了两口就没了什么胃口。便放下筷子端起茶盏有一口没一口的抿着,一边随意的听着邻座几桌的闲谈。
只听一旁坐着的几个小贩模样的人在那里嘘声嘀咕:“我听说啊,昨天又杀了一批,死得那可叫一个惨。头都扔出去喂野狗了!”
“可不是吗?那项国公一向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我看这下是没人敢去他府上做食客了,命不想要啦?”
“欸,我看不见得,这两天不又在重金招纳贤士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要钱不要命的多了去了。”
“哎…那倒也是,现在谁还不是在刀尖儿上讨生活?世乱时艰啊……哎,不说了不说了,喝酒!”
水宿亦在一边静静听,此时看了白靳潜一眼小声道:“少主,我也听说那项国公是个草莽之人,生性残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投奔他呢?万一他哪天一个不高兴把我们俩…”水宿说着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怎么办?”
白靳潜一笑:“越是性情暴戾的人越是容易掌控,只要手段得法,再猛的虎也照样可制于鼓掌之间。不必担心……我们还要靠他这根棍,搅浑秦国这池水呢。”
正说着,只见几个穿着公服的带刀侍卫大喇喇的晃到客栈里抓过掌柜就问:“昨天有没有两个从金陵来的人,是住在你们这儿吗?”
那掌柜偷瞄了一眼他们的腰牌佩剑竟是项国公府的人,顿时吓得腿抖得如同筛糠,结结巴巴道:“回…回几位官爷……正…正是那边坐着的两位。”
那几人顺着掌柜手指的方向二话不说便冲了过去,那掌柜见状艰难的咽了口唾沫,不知那两个外地人初来乍到,怎么就惹上了这么大的刺儿头,几乎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小店要被砸个底朝天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几人冲到半途陡然在那两人身边不远不近的地方停住,态度顿时一百八十度转变,朝着那个稍年长些的恭敬道:
“敢问公子可是金陵林隐堂的白靳潜白先生?”
白靳潜微抬起头对那人一笑道:“正是在下。”
那人闻言忙拱手一揖,道:“见过白先生,小的们是奉穆大人之命来迎接先生的。外面已经备好了车轿,请先生移步国公府,穆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白靳潜本来答应了水宿先带他到外面的闹市里多逛几日再去办正事的,可没想到项国公的消息这样灵通,又或者是林跃本在这里安排的探子消息比较灵通,他们这边才刚到那边就已经急匆匆的找上门来了,不过反正迟早也是要走一遭,如此也没必要推辞。
只是水宿明显不太乐意,气冲冲的朝那几个人直瞪眼,去国公府的一路上都嘟着嘴,一句话也不说。
直到白靳潜没办法,答应他等见过项国公一定带他出来把好吃好玩的都吃逛个遍,这才一脸得逞的样子笑得傻兮兮。
车轿穿过闹市,又穿过两条弯弯曲曲的小巷之后眼前便是一片豁然开朗,国公府威严的府门赫然矗立着,一种无形的森森气场让前一刻还在有说有笑的水宿都不自觉地安静了下来。
车轿稳稳地停在府门前,那侍卫恭恭敬敬等白靳潜下轿,从旁引着二人入府。
侍卫手中有令牌,又是熟门熟路,几人就这么走过一个又一个桥廊庭院,越过一道又一道森严的防卫,倒是一路畅行无阻。
不经意间抬眼一看,眼前一块宽大的金丝楠木匾额上刻着的“贤居堂”三字,那侍卫带头停了下来,
道:“这里就是议事堂了,请先生在这里稍等,我去通报大人。”
“有劳了。”
“先生客气。”
贤居堂的门此刻正半掩着,还未待侍卫走近,一个白瓷杯子竟冷不丁从门缝里飞了出来,那侍卫眼疾手快,一个闪身将将避过,那杯子速度不减,就这么继续向前飞冲,待那侍卫反应过来自己身后还有白靳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侍卫惊出一声冷汗之际,白靳潜身后的水宿身形一闪,随即便见那杯子陡然改变了方向,撞在一旁的树根上,碰个粉碎。
侍卫刚想向白靳潜赔礼,却见屋门猛然被人一把推开。屋内随之传来如平地惊雷般的怒吼:
“废物!拖出去!给我拖出去砍了!”
白靳潜朝屋内看去,只见一人瑟缩着身体俯伏在地面上,一边拼死抵抗者两旁人的拖拽一边哭喊道:
“大人!属下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花魁姑娘是他们的人!这才一个不小心…属下真的是不知情!属下对大人绝无二心!天地可鉴!请大人饶命!请大人饶命啊!”说罢不住把头往地上磕得砰砰响,看来真是吓得不轻。
再看他身前立着的那人,身长足足七尺有余,魁梧壮硕,须髯如戟,一身华服俨然的气象,想必便是秦国太尉,项国公穆尔卫大人了。
只见穆尔卫毫不动容,飞起腿对着那人面门便是一脚,直踹得那人一下子背了气,连头都抬不起来。“你一个不小心?你一个不小心是不想要了老子的命?!老子这头才刚丢了并州,你这边就有功夫去青楼找婆娘不算,还让人逮着把消息给抖搂出去?你让京城的百姓怎么看我?老子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给我拖出去!立刻给我拖出去砍了!”闻言,拽着他两臂的侍卫也不敢怠慢,猛的一使力气,那人便如一摊烂泥般被拖了出来。
水宿看着那人渐渐被拖远,不禁与白靳潜面面相觑。那侍卫没想到今天这一来就不巧竟正碰上穆尔卫在气头上,心里直道出门没看黄历,点着步子小心翼翼走到穆尔卫身边道:
“大人……白先生到了。”
“让他进来”穆尔卫背着身子,手一挥,颇不耐烦。
白靳潜见状上前一礼道:“在下白靳潜,见过穆大人。”
穆尔卫闻言甫一转身,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上下打量了半晌,
挑眉道:“你就是白靳潜?……听刑部卫存大人举荐说你是金陵林隐堂中的第一神医,医术造诣极高。但从不轻易露面,更加不会轻易替人诊治,纵是天潢贵胄都不见得能见上一面……我当是有多深不可测,今日一见也不过一届文弱书生嘛…我看这医术也未必有传闻中的那么高绝吧……”
白靳潜一笑,道:“医术高低从不是从外表判断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从外表便能让人一眼看穿,那未免也太肤浅了些…听闻大人罹患头风多年不愈,深受其苦,寻遍名医依旧无果,倒不妨让白某一试,或可为大人解忧。”
“试倒是可以,我被方才那厮气得这会儿正好有些头痛。只不过我已经被那些个自称名医神手的江湖郎中折腾烦了,所以我只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一炷香之后我的症状若还是没有缓和……”
穆尔卫说着顿了顿,眼中一抹戾气一闪而过
“我就即刻杀了你!”
“你!”水宿闻言如触电般顿时警觉起来,手一下子就按上了剑柄。白靳潜不动声色的暗中轻拍了拍水宿的手,神色依旧如常,对穆尔卫一揖道:
“就依大人所言。”
言语间,穆尔卫的头愈发痛得紧,被侍卫搀扶着蹒跚进了里屋,神情极为痛苦的半倚在榻上。
白靳潜亦随之入内在穆尔卫的榻边坐定,从药箱中取出脉枕垫在他的手腕下,三根修长的手指则轻轻搭上了手腕的寸关尺三脉,微闭上眼睛,指间的力道由轻到重又由重到轻,片刻后,缓缓收回手对穆尔卫道:
“我观大人脉象弦而数,故病邪究其源头应当在肝。而且大人面色赤红,频出虚汗,且易躁易怒,怒则气逆,气逆则肝阳上亢,气机不舒,营卫失和,上蒙清窍,以至邪气冲犯巅顶,故而才致大人痛症反复不愈。我先替大人施针镇痛,再以祛风泻燥的汤药辅之,当可以暂安风邪缓解病症,大人以为如何?”
“行行行,就依你,你快点给我治,我快疼死了!”穆尔卫烦躁的挥了挥手,眼睛和眉毛皱得都快挤到了一块儿,看来确实是痛得厉害。
白靳潜于是取出针盒,分别取了太冲,百会,神聪四穴,气海等几个穴位分别下针。
不到片刻,果见穆尔卫的脸色有所和缓,赤红如潮水般消退,眉头也渐渐舒展了开来。
又过了一会儿待白靳潜开始慢慢拔出金针,穆尔卫原本紧闭的眼睛已经微微睁开,嘴唇轻动了动道:
“水。”
一旁守着的侍卫闻言忙不迭端来一碗水恭敬递上,穆尔卫半撑起身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用衣袖揩了揩嘴,看着不远处记时用的已经燃了一半的沉香一挥袖道:
“把那个撤了吧。”转而竟颜色温和的看着白靳潜。
白靳潜一笑:“大人感觉好些了吗?”
穆尔卫亦用嘴角扯出几分笑意,点了点头。
“我已经让人去准备汤药了,待一会服完药,大人再静养片刻,只要这几日大人不再大动肝火,便应当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穆尔卫听罢,摇了摇头,一副烦忧无奈已极的样子,和着乌黑胡子中偶尔露出的几根白须,竟有几分迟暮凄凉之感。白靳潜见状顿了顿道:“大人似乎是有什么心事……白某斗胆,大人若不介意,不防说与白某,总好过憋闷心中,再增积郁。”
穆尔卫叹了口气,道:“方才我在前堂训人的那些话你都听到了?”
“听见了几句。”
“不瞒先生,说来也是丑事一桩。方才那厮本来是到青楼去找婆娘快活的,哪曾想那婆娘竟然与御史台有勾连,使出一身狐媚妖术引得那厮喝得烂醉,口无遮拦的满口胡言乱语,说我私吞军粮,收受贿赂才至并州兵败,让御史台的探子逮个正着。
主上那儿参我的折子早已经雪片一样漫天乱飞了,此番与北燕交战失利,又出了这等事……”
一边的侍卫以为穆尔卫一定是病傻了,这种隐秘之事竟也随便对一个不知底细的大夫乱说,忙清了清嗓子提醒穆尔卫道:
“大人,此时事关机要,恐怕……”
没想到穆尔卫反而没好气道:“恐怕什么恐怕,平日里吃喝嫖赌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们怕过?我要是一直憋着这口恶气没处出肯定得少活十年!你给我出去!要和白先生聊聊。”
那侍卫自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退了出去。
穆尔卫等他离开后,重重一声长叹:“主上现在不愿意见我,我现在就是有口也难辨了……唉……我和先生说这些先生也不会明白,先生就当是听一个病人发发牢骚吧……”
白靳潜听罢沉吟片刻,转而道:“大人不必如此忧心。大人若不介意,其实白某倒是有一些拙见,只是不知大人愿否一听。”
“哦?”穆尔卫闻言颇有些意外,将身子直了直道:“先生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白靳潜顿了顿,道:“白某以为,大人方才说主上现在不愿意面见大人,说明主上对那些谗言至少已经信了三分,但却又没有立即处置您,说明他的心中也尚存疑虑。白某虽非秦人,但穆大人的灼灼威名,赫赫军功白某亦早有耳闻。对于大人的处置如若轻率失当,恐怕引起朝野骚乱,在此外乱之时再添内忧。所以白某斗胆猜测,主上迟迟不作明确的裁定也当有这层顾虑。
再者,具本参劾大人的那些人手中一定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一招置大人于死地,故而才先施一计在主上与大人之间制造罅隙,再顺着这罅隙缓图后招……
为今之计,大人只有先设法见主上一面,方能破此僵局。”
穆尔卫听罢神色愕然中带着几丝复杂,楞了片刻复又恹恹的吁气道:
“我当然知道要见到主上才能有办法喊冤,但是主上就是不见我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大人别急。……方才听大人说此次并州作战不利,这边紧接着就又出了青楼之事,大人不觉得有些太巧了吗?这一切听起来倒像是有什么人早就设计好了一样。”
穆尔卫皱了皱眉头,默默将近来的所有事情在脑中滤了一遍,转而道:“先生这么一说倒还真是,而且在并州的时候我带兵攻城,让人在城外埋伏,声东击西,可谁知燕国的慕容老贼竟像是先知先觉一般非但不中计,反倒使我军为计所累,吃了大亏。不过现在再想想,总觉得有些蹊跷……难道是我身边也出了内鬼?!”
白靳潜笑了笑,并未作答,穆尔卫左思右想越发觉得是这么回事,否则那慕容老贼难不成还能未卜先知不成吗?
就是说方才那件事,长安城秦楼楚馆里的姑娘那么多,怎么就偏偏让那个糊涂蛋撞上一个和御史台有勾结的娘们儿?
不由恨恨道:
“最近总听凭虚阁的人说近来细作猖獗,一定要加强防范。我还以为是那帮妖里妖气的探子危言耸听,根本没当回事儿,没想到这还真有人敢蹲在我头上拉屎……要是让我抓住是哪个兔崽子,我非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大人,白某倒是有一计,或可引那细作出来。”
“哦?先生有办法?”
白靳潜点了点头,“只不过在这之前,大人要先做一件事情。明日早朝,大人可再去求见主上。主上若仍是不愿见大人,大人便长跪殿外称已有夺回并州的良策,请求戴罪立功。主上必定正为此事发愁,想来会愿意见大人这一面。如此待主上同意让大人再次挥师并州之后,我这一计才好施行。”
“可是我并没有所谓夺回并州的良策啊,这么说岂不是欺君罔上吗,到时战事若仍是不利你让我拿什么和主上交代?到时候十个脑袋估计都不够砍的。”
“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大人如今处境不妙,带兵在外,总好过现在这般被困在内。至于这之后的事白某自有一些手段可以协助大人,大人不必担心……”
白靳潜说着话锋一转:“白某知道自己的言辞有些唐突,但大人既然愿意对白某倾诉,白某便斗胆给大人一些提议,就如诊病一样,大人若信得过白某,便可一试。若是信不过,就当白某什么都没说过便好。”
穆尔卫盯着白靳潜细细打量了半晌,越发觉得此人绝非普通的江湖郎中,更像是有备而来,恐怕这次来为自己诊治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必定另有所图。况且他又是经刑部侍郎举荐才来到府中,一个外邦人竟已与刑部官员相熟,可想而知此人的背景不会简单。不过这医术高明倒似乎不虚。只是没想到他竟然第一次见面就如此单刀直入丝毫不加掩饰,倒颇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但既然他已经横冲直撞的进了自己的府里,与其打草惊蛇,还不如先装傻充愣姑且先顺着他的路子来,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是谁的人,又想在这儿耍什么花招。说不定这条长线之后会是一条意想不到的大鱼。
穆尔卫想着狡黠一笑,道:“不瞒先生,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任何一根救命稻草我都不会轻易放过的,先生既愿为我费心,我自然愿意一试,总要好过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但…先生若是仗着我的信任想趁机跟我耍什么花招……那我劝先生还是省省吧,先生应当明白惹怒我的下场。”
“白某自然明白,若是没有把握的事,白某也不敢在大人面前胡言。做与不做全凭大人决断,但若大人依计而行仍不免刑狱之祸,到时白某任由大人发落。”
“好!你够胆量。那明日我便姑且一试。”
这时,水宿正好端着药进来,白靳潜将药递上,起身一揖道:
“如此,便请大人先服药休息,大人今后若是有什么需要,白某随时恭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