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中国元代建阳地区儒释道三教流行,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空前繁盛,坊刻通俗文学图像呈现儒释道教化与伦理道德叙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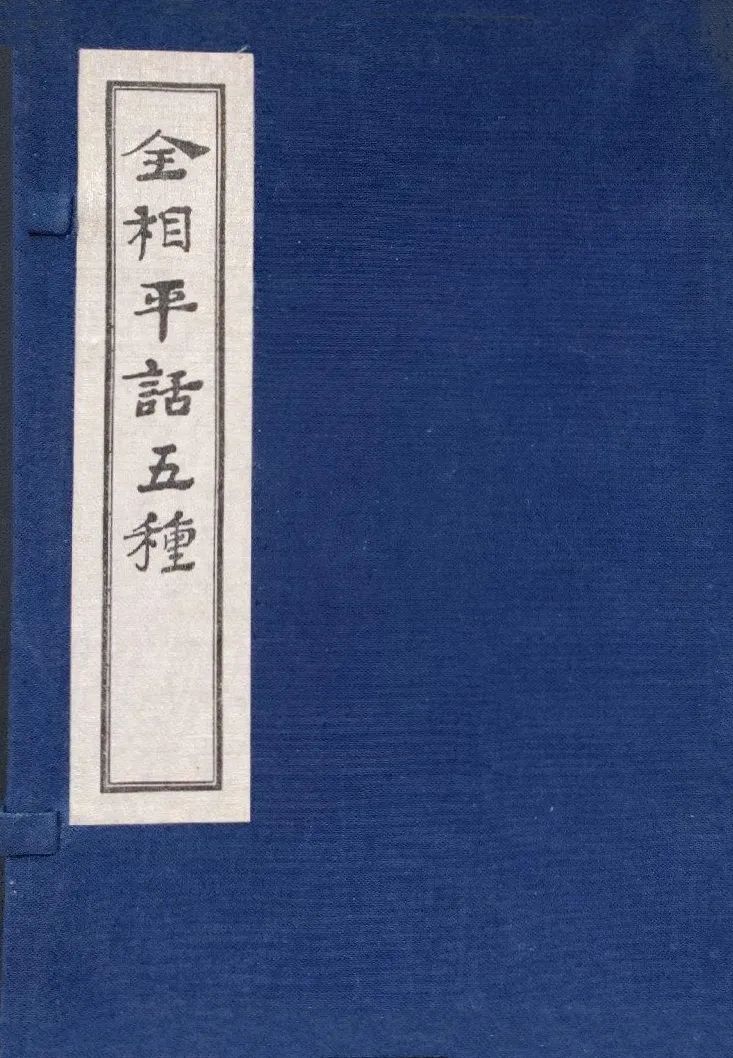
文学古籍刊行社版《全相平话五种》
《全相平话五种》小说图像以一套规整的礼仪图式表征儒家政教体系和大众宗教思维,反映出儒道佛制度化宗教在社会中的伦理接受与信仰标准。本文所探讨的宗教,指的是元代制度化的儒道佛三教,杨庆堃、金泽等先生已有界定。[1]
目前,国内外关于《全相平话》图像的研究围绕语图叙事和版画艺术展开,例如日本学者泷本弘之的专著The Colletive Edition of Five Completely Illustrated Ping hua,主要探讨了全相平话的版画风格与叙事特点,尚未见从宗教文化视角展开研究的相关成果。[2]
作为元代文化书籍兼通俗小说,《全相平话》插图具有儒、道、佛三教教义的复杂性,图像建构了以儒家政教为核心的视觉空间,并杂糅了道教、佛教的教义伦理,反映出元代建阳地区民间的宗教观念与信仰价值。

二、图像主旨:“天命无常”宗教观与儒教规约
元代统治者实施开放兼容的宗教政策,建阳地区儒教、道教、佛教三教盛行,儒教教义与佛道思想融合,三教同源、三教归一的现象十分突出。
作为儒释道大众接受的直观文化代表,建阳地区通俗文学图像《三分事略》《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五种》等,呈现儒家政教秩序与佛道宗教观念的多维融合。
其中,建阳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刻有上图下文式版画246幅,采用连相形态刻画战国至三国期间的讲史故事,全面展呈出儒释道文化视域中王朝兴衰、战争角逐、神魔斗法、传奇英雄等视觉景观。小说图像符号通过宗教观念与权力秩序之间的关系,对多元宗教文化展开视觉实践。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
《全相平话》图像的表意策略,是借助插图符号建构儒教秩序与佛道“天命无常”观念的复合性主旨。杨庆堃指出“天命无常”概念是儒教在借鉴佛教、道教阴阳五行说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政教意义,天命思想为皇权在政治上整合这个庞大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而天命具有统辖地方神与信仰的权威性,君王、百姓扰乱了宇宙和谐秩序,天的反应是警告在前,惩罚在后。在社会层面,天命被儒家思想接受,并形成了象征着强大的,富有道德内涵的政教力量体系。[3]
《全相平话》通过宗教图像的叙事,构建出儒教规约下的“天命无常”观,为便于论述,我们统计出小说插图叙事条目,如表1所示。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全相平话五种》
表1 《全相平话五种》佛教、道教叙事图像统计表[4]
小说
名目
插图
数量
佛教道教
叙事图像
宗教图像占百分比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
扉页1幅,卷上15幅,卷中15幅,卷下12幅,共43幅
纣王梦玉女授玉带图;九尾狐换妲己神魂图;宝剑惊妲己图;文王遇雷震子图;宝钏惊妲己图;金盏打妲己图;殷交梦神赐破纣斧图;皂雕爪妲己图;文王因囚姜里图;西伯吐肉成兔子图;雷震破三将图;比干射九尾狐图;文王梦飞熊图;太公破纣兵图;武王斩纣王妲己图
35%
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
卷上14幅,卷中14幅,卷下14幅,共42幅
齐王贬二公子图;燕王筑黄金台招贤图;田单火牛阵破燕兵图;孙子困乐毅图;乐毅请黄伯杨图齐图;迷魂阵困孙子图;鬼谷下山图;独孤角入迷魂阵图;鬼谷擒毕昌图;鱼叟送阴书图;伯杨乐毅投降鬼谷图;四国顺齐图
29%
全相秦并六国平话
扉页1幅,卷上20幅,卷中15幅,卷下16幅,共52幅
王翦败张晃图;周光刺王翦图;邹兴射王翦图;韩惠王薨图;王翦唬倒韩王图;王翦灭韩国图;秦齐大战图;始皇封大夫松图;打始皇车图;焚书坑儒图;沛公当道斩蛇图;始皇崩沙丘图
23%
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
扉页1幅,卷上12幅,卷中13幅,卷下12幅,共38幅
汉王葬项王图;刘武刺汉王图;韩信下六将为主报仇射吕后图;杀彭越扈辙触堦死图;英布射汉王图;汉高祖升遐立惠帝图;惠帝游凌烟阁图;吕后祭汉王图;吕后梦鹰犬索命图;诛吕氏三千图;汉文帝归长安图;汉文帝登位图
31%
全相平话三国志
扉页1幅,卷上23幅,卷中24幅,卷下23幅,共71幅
天差仲相作阴君图;仲相断阴间事图;孙学究得天书图;先生跳澶溪图;玄德哭荆王墓图;赤壁鏖兵图;刘备托孤图;孔明木牛流马图;秋风五丈原图;将星坠落孔明营图;
14%
表1宗教图像叙事数量共61幅,所占百分比较高,此类图像刻画佛教、道教神话景观,如《武王伐纣书》“文王遇雷震子图”道教神仙雷震子形象描绘,《乐毅图齐平话》“破迷魂阵图”道教神仙用符咒斗法,《全相平话三国志》“仲相断阴间事图”佛教轮回场景等。插图辅佐小说情节叙事,既具有宗教叙事特征又表现出视觉上的伦理秩序。
《全相平话》宏观叙事框架建构出“天命无常”阴阳五行观念,基于讲史纲要,编者虚构天神护翼、神佛助厄、仙魔斗法、因果轮回等宗教叙事,增设的神仙模式熔铸“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儒教伦理。
那么,与小说文本关联的视觉图像是如何反映的公共事件中儒教主题的,画工又是如何整合佛教、道教等宗教形象的?
讨论《全相平话》图像儒教伦理认知的前提,首先是插图如何塑造宗教形象满足儒家政教主旨。
《全相平话》插图通过道教、佛教神话形象的刻画,精心构建出儒教政教纲常。以《前汉书续集》图像系统中的吕雉形象塑造为例,文本语境中的吕氏在汉初王朝运势之中扮演核心角色,她辅佐君主平天下、斩韩信,为巩固权势杀害英布、彭越等贤良,篡位后试图拥吕氏改元换姓。

图1:《前汉书续集》卷中“韩信下六将为主报仇射吕后图”,道教“真龙”护佑吕雉
小说系列插图将吕氏置于“天命”与“儒教”视觉场域中,“韩信下六将为主报仇射吕后图”绘臣属天子势力的吕后未谋害贤良、悖逆朝纲之前,孙安六将因报韩信仇射杀吕雉,而“吕后终托着皇帝福荫,忽见一条金龙护身”逃过劫难(图1,一旦吕氏违背天意打破秩序体系,画工则以“梦鹰犬索命图”昭示天降灾厄(图2),随即吕氏三千被刘氏正统诛杀殆尽。

图2:《前汉书续集》卷下“吕后梦鹰犬索命图”,吕雉临朝自立君主梦鹰犬灾厄
透过“真龙”“鹰犬”道教符号,图像意志集中表达神性加持下的国家秩序。这里图像的天命模式为“君权神授”,插图中“真龙”刘邦助吕后幸免于难,反叛六人则顺天谴自杀而亡,刘邦逝世吕后违背天命自立天子,则“天夺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祸也”。
道教符号建构出图像视觉性中普遍、稳定、统一的形象,物化的龙、鹰、犬携带传统印记,承担唤醒观者文化、情感、理性等体验。
前文论及,建阳社会面盛行的儒教思想是朱熹依据阴阳五行说天命思维“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改造,核心在于类比金、木、水、火、土“天地五德”相生克,形成社会“阴阳五行之气,健顺五常之理”,在政统则表征为儒家思想中纲常秩序。
《前汉书续集》小说插图昭示的“天命无常”模式与儒教纲常“仁义礼智信”紧密关联,画工将吕雉行为置于正统礼教围观中展开,天意护佑、天降灾厄取决于吕雉是否悖逆儒教伦理。

图3:《前汉书续集》卷下“吕后祭汉王图”,刘邦携韩信神魂箭射吕雉
需要注意的是,卷下“吕后祭汉王图”叙吕雉自立天子后祭拜刘邦,插图则以刘邦携韩信、英布、彭越诸人灵魂讨伐吕氏,韩信张弓搭箭射杀吕后,此时“真龙”刘邦位于群臣之中(图3),与吕雉形象构成敌对关系,吕后随即左乳中箭,与图1真龙护佑构成鲜明对比。
因而图像所建构的“天命无常”旨趣即天命正统,代表儒家秩序的五德之君具有神圣地位,而皇权或世俗出现反叛、谋逆、破礼、祸乱等违反儒家“健顺五常之理”的行为,宗教神借助神化征兆予以警示惩戒、转移符瑞。
《前汉书续集》通过质朴的道教、佛教图像符号系统,表现出儒教政治中的仁义、孝悌、忠信伦理主旨。天子君权是为神授,权力运作、王朝更替需顺应儒教“阴阳五德”,宗教神以“天神异像”保护君权,宗教神的庇护表征天命正统、符瑞的合法性,反之,天子违反阴阳五德,则会受到天意惩罚——上天通过无形意志改元易姓。
《武王伐纣书》卷上“纣王梦玉女授玉带图”“九尾狐换妲己神魂图”“文王因囚姜里城图”分别预示着“天命无常”宗教观,前二幅绘商纣王宗庙见玉女起淫色,天降狐妖化作此女形象祸乱朝纲,第三幅绘周文王被囚姜里城时有天凤来仪,文王之子武王随即推翻商王朝。
《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天差仲相作阴君图”以司马仲相入地狱审理韩信、彭越、英布开始,金甲神人传达天命——三人转世为曹操、刘备、孙权分取汉朝天下,司马氏顺天意统一三国。
此外,《秦并六国平话》“周光刺王翦图”“沛公当道断蛇图”,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燕齐两国“阴阳斗法图”系列,通过神授君权、神灵护体、神降符瑞等天命模式辅佐王朝建立。此类小说插图通过天凤、金龙、飞熊、天公、神兵、妖狐、地狱判官、罗刹等佛教、道教神魔形象的塑造,在天命无常主旨中体现出儒教纲常秩序规约。

建安虞氏刊本《秦并六国平话》
总体看来,小说图像中的神仙形象是底层大众关于道教、佛教的想象与认知,它的艺术媒介转译交织着“天命无常”观念。这些图像经由直观视觉的演绎、搭建,与儒教纲常伦理形成强烈的交叉互动,建构视像关系中“天命无常”的视觉主题。

三、宗教图式:儒家政教秩序的空间表现
儒教作为宗法性伦理宗教,其核心是政教礼仪与政教秩序。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天命”观念,上至帝王下到普通民众,其中就包含着道德原则的宇宙秩序,儒教借鉴佛教、道教天人思想,并将政治与教化紧密结合。[5]
正如范丽珠所云:“儒教、道教、佛教宗教体系始终关注于政治伦理和信仰教化之于社会秩序的多方有效性。”[6]《全相平话》小说图像宗教图像的书写,即是儒家政教秩序的空间表现。就宗教图像生成而言,文本强调的伦理教化决定了其秩序来源。
如《乐毅图七国》“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一不忠者,佐二主;二不孝,远离父母;三不义,苦谏帝王行邪”、《秦并六国平话》“吾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等,构成图像反映的儒教政教伦理基础。

图4:《武王伐纣书》卷下“武王斩纣王妲己”,道教仪式与儒家秩序的空间建构
《武王伐纣书》结局关要有“武王斩纣王妲己图”,绘商纣王败于周武王后被斩仪式。插图右页周武王端坐中央,官吏持笏立于两旁,侍从拥华盖站于背后(图4)。
图像左侧绘斩首后的妲己化身九尾人面妖狐,被姜子牙持降妖镜斩杀于地,亡国之君商纣缚跪于地等待“天授神斧”行刑(图4)。
图像右侧通过帝王仪式塑造出权力中心场,此时周武王与跪地的商纣形成以身份等级为逻辑的“尊卑”人物结构秩序,武王为尊、纣王为卑,道家姜子牙与九尾狐斗法显示出道教神魔的在场。
图像中武王以端坐俯瞰的姿态监视全局,神魔斗法与纣王被斩皆在儒家秩序审视之中,画工将图像君主、道家神魔、小厮设计在严密的“尊卑”儒家伦理框架内。小说插图神仙修辞符号显现天命无常意志,形构儒家秩序的空间形态,表现出儒家伦理规约下世俗宗教与王权社会均需顺应纲常秩序。
无独有偶,《乐毅图七国后集》结局“七国顺齐图”,绘齐国战胜燕、楚、秦、魏四国联军,四国朝拜齐国并每岁纳贡,图像表征出典型的儒家仪礼秩序。
图像绘齐王政权居左,四国政权作为顺臣居右,搭建出以左为尊的符号秩序,齐国政治集团齐襄王居中端坐,左右分列道教神“鬼谷子”“孙子”并作拱手礼左右而立(图5),山水屏风、道教神形象、顺臣朝拜等图像符号辅佐君王,构成儒家政治权力核心“齐襄王”。

图5:《乐毅图七国后集》卷下“七国顺齐图”,儒家空间形态书写
插图以代表儒教仁义正统的齐国为主题,左右辅佐为道家通晓神魔仙法的鬼谷子、孙子,对话违悖纲常伦理的四国侵略政治,形构空间仪式形态的强烈反差,隐喻着儒家权力秩序统摄道教,诸侯之间需顺应儒教仁义伦理纲常。
在图像秩序系统中,插图中的人物尊卑、神魔大小、职官主次、仪式繁简、建筑高低表征着儒家政教秩序的政治、社会空间。
《全相平话》通过一套较为完备的秩序系统反映图像伦理含义,其主旨是儒教宗法等级的普适性。小说图像塑造的佛、道判案场景,即是儒家政教尊卑、忠孝观念的空间表达。
《全相三国志》卷上有“仲相断阴间公事图”,绘司马仲相应天神意志入地狱审理《前汉书续集》中韩信、英布、彭越冤案,文本地狱场景塑造为“上殿,见九龙金椅。仲相上椅端坐,受其山呼万岁毕,八人奏曰”。

图6:《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仲相断阴间公事图”,佛教地狱景观的塑造
图像空间中,右侧图像绘司马仲相端坐中央,身着平天冠、龙袍、无忧履、玉束带、佩剑,前置公案桌、后立天子屏风,侍从八人站立左右,穿戴长翅帽、儒袍、朝笏,左侧图像绘韩信主仆跪姿,彭越、英布、汉高祖、吕太后站姿依次庭审(图6)。
图像空间构成“尊卑”等级秩序,画工绘制了佛教中的“地狱场景”。图像地狱书写无关乎牛鬼、马面、蛇神等佛教阴司形象,而意在突出儒教权力形态的天子、公堂、儒士,其设计逻辑与儒教政教秩序场景相同。
宗教图式的“尊卑”塑造及“弃神”行为,象征着儒教纲常伦理的渗透,彰显出底层大众宗教神思维的规约性。神化仪式的梦境绘制同样采取这一策略,《武王伐纣书》“殷交梦神赐斧图”绘太子殷交逃离朝歌夜行至神庙,梦见“(神)与太子饮之,又与大斧一具,可重百斤,名曰破纣之斧”。
如图7所示,插图右侧绘卧睡殷交,左侧绘神仙赐斧仪式,神人、侍从、桌子搭建出秩序空间等级形态,天神所赐“神斧”则由穿着长翅帽、儒袍的官吏授予。

图7:《武王伐纣书》卷上“殷交梦神赐破纣斧图”,道教天神场景的塑造
道教“仙人赐斧”仪式空间属画工逃离文本的独立塑造,神化形象绘制为儒教政治秩序仪式场景,反映了儒家政教的大众景观。
天神依据“太子具说父王不仁无道之事”,赐斧子用以斩杀纣王,说明纣王违背纲常五德,天命改元易姓的图像意志,表现出大众对儒家仁义礼教伦理的认同与接受。
再如《武王伐纣书》卷上“纣王梦玉女授玉带图”“文王梦飞熊图”、《前汉书续集》卷下“英布射汉王图”、《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将星坠孔明营图”、《秦并六国》卷下“始皇令王翦伐赵图”等宗教叙事图像,画工借助天子服饰、文臣长翅帽、武将盔甲、儒袍(圆领袍)、天子屏风、公堂匾额、审讯案台、执事仪仗等秩序符号建构儒家权力场,仙佛斗法、神魔助异、妖鬼罗刹宗教符号辅佐儒家政教伦理的空间形态塑造。
因而我们认为,《全相平话》小说图像是画工基于儒家政教秩序的概念表达,它经由道教、佛教语图符号修辞的现实性模仿,弥补读者对神仙形象概念的残缺,同时刻画儒家政教观念中的尊卑秩序与伦理等级。
综上,《全相平话》宗教图像呈现出通俗文学作者、画工、刻工的大众认同,刻画出儒教政教秩序空间。画师主要通过佛教、道教形象的塑造,对小说图像进行儒教尊卑秩序的排列。小说语图符号的建构,折射出儒家政教伦理对宗教图像空间形态的影响,昭示了中国早期小说插图视觉审美探寻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宋元平话集》

四、宗教景观:儒道佛仪式的大众建构与道德教化
《全相平话》中的儒道佛叙事图像,塑造了王朝祭祀、祈祷忏悔、作法施术、诵念经典、神魔判案等具有仪式性的宗教活动。埃米尔·迪尔凯姆 ( E.Durkheim)认为“仪式是所有宗教的一个要素,它与信仰一样至关重要。”[7]
宗教美术史家华莱士亦指出:“宗教行为的基本范畴,只能在称作仪式的,组织化为前后关联中发现。与此相似,这些仪式本身以及相关的信仰,乃是一种更大的复合体的组成部分。”[8]
华莱士将多种仪式的复合体定义为崇拜制度,多种崇拜与信仰混合形成社会宗教。宗教仪式反映了制度的合法性、神圣性,维克多·特纳指出:“宗教仪式是对神秘的存在或力量的信仰,这些存在或力量被看做所有结果的第一位的和终极的原因。”[9]
由此可知,宗教仪式是大众对神圣者、神秘现象产生的认知、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崇拜行为。《全相平话》插图建构了宗教仪式的大众观看之道,图像叙事、神魔形象等语图符号建构的仪式景观,是底层大众接受儒释道三教折衷观念的展现。
《全相平话》宗教仪式图像则通过三教道德教化观念的塑造,表现出了大众世俗的宗教伦理认知。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语法研究》
《全相平话》宗教仪式图像的建构,反映出元代建阳地区儒道佛三教折衷的道德教化观念。众所周知,元代儒释道三教鼎立,彼此相互斗争、妥协,僧道、信徒及传教方式呈现世俗化特征。[10]
《元史》记载:“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僧人可以学儒士从政、经商。元代主流道教的宗师、教众具有儒士色彩,同样有着鲜明的合一三教和世俗化特征,盛行于南方的正一道,入世教义与世俗道德规范相联系,强调“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世间上品好人”宗旨。[11]
佛教、道教教义与儒教纲常“仁义”“忠孝”结合,形成世俗大众崇拜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这种宗教观念体现在社会法律、道德层面,是“仁义礼智信”德行与正义,而体现在宇宙秩序层面则是“天地五德”发生与消亡的自然规律。
《全相平话》中的神魔判案图、王朝祭祀图,将神圣力量与道德伦理相结合,集中表现出元代建阳社会的信仰仪式。
例如,《全相平话三国志》有“天派司马仲相做地狱君主”仪式图,叙述司马仲相入阴间断冤案一事。

图8:《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天派司马仲相作地狱君主”
如图8所示,图像右侧绘司马氏穿着天子服饰端坐于地,八位天神站列于左,判案仪式场景位于地狱。图像主题借助人间、地狱因果轮回模式,将天神形象与人间伦理秩序相结合,宣扬天命无常、善恶报应的伦理观念。与之对应的小说文本,则进一步阐释了大众思维中佛教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图像中八位天神与司马仲相交谈内容为:
陛下道不得个随佛上生,随佛者下生。陛下看尧舜禹汤之民,即合与赏;桀纣之民,即合诛杀。我王不晓其意,无道之主有作孽之民,皆是天公之意。
文本内容带有鲜明的佛教宣讲内涵,佛教上生、下生源自于《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指佛教“弥勒上生净土”“弥勒下生救世”观念,意在教化世俗明心见性,注重德性修行,最终抵达大乘境界。
编者将佛教教化与尧舜仁义、夏桀商纣暴虐相类比,指出佛教神圣力量与儒教仁义秩序联系,明确了天道公正、善恶有序的政教合一信仰。也就是说,世俗眼中的敬佛、敬天信仰与儒教道德纲常相结合,从而形成普遍认可的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体系。
小说图像判案仪式场景,建立在天道轮回与善恶报应的文本语义之中,通过司马仲相神仙信仰仪式表现,实现佛教劝善立德与政治伦理秩序的结合。

《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
正如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指出的“政教合一”结构,“社会顶点有一个神圣的位置(sacredspace),那些控制这个位置的人,具有超越性力量,足以改变社会”。[12]
图文符号书写的神魔判案、王朝祭祀等宗教仪式活动,建构出底层儒教秩序与佛教教化的互动关系,大众借助超越性的力量,目的是为追求天人互动,实现社会伦理中的公序良俗。
小说插图道教仪式的建构,同样表现出忠孝仁义教化观念。从元代道教教义及仪式看,道教提出的气、阴阳、五行、八卦教义,是对宇宙物理构成的社会伦理模仿,仪式则是连接天人合一的途径。
元代道教盛行的斋醮、祈禳仪式,包含祭孤、祝寿、庆贺、接驾、祈祷等多种形式,这类仪式被社会广泛接受,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祈盼通过仪式驱邪避害、赐福禳灾。宋元时期,伴随着道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人与神交流的道教仪式被改编成通俗文学叙事题材。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梅林宝(Mark Meulenbeld)认为,宋代以后,这些仪式成为了叙事虚构作品的素材,并且同样的神祇会出现在仪式和小说中。[13]《全相平话》包含大量的祭孤图、祈祷图,这些具有道教仪式的图形,预设了前世因果、善恶业报的伦理主题。
例如,《武王伐纣书》中有“文王祈祷图”,小说文本叙周文王被商纣关押姜里城后,每日占卜问卦:“长把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神将大将军,使六丁六甲力左右将军,摘其中十干五行,二十八宿定分,八卦爻象,逐年逐月逐日逐时,知吉凶主事。”
周文王借助道教祈禳仪式,预知人间灾福及命途吉凶,进而关心百姓农业收成、疾病灾伤,而作为仪式的回应,天神降“天凤符瑞”,以显现周文王仁义、爱民之心。
小说插图聚焦“天凤来仪”仪式,图像中周文王端坐于地,左手持龟壳、右手持石子,地面则置有祈禳之用的符箓文书(如图9所示),代表神意的“天凤”立于其侧。

图9:《武王伐纣书》卷中“文王囚姜里图”,天降符瑞于周文王
图像道教仪式的建构,再现文本符号中天、人沟通的神化场景,而图像“天凤来仪”则表征出天命无常与善恶业报的主旨。
一方面,图像叙述纣王暴虐百姓、杀害忠良,违背“忠孝仁义”伦理德行,因而神意改元换代,选择仁义爱民的周文王为君。
另一方面,图像仪式表现出大众对神秘力量的宗教信仰,无论大众还是帝王,其行为均需符合仁义、孝悌、善良的伦理规约,违背道德秩序的个人或君主,则会受到神的谴责与报应。
与此相同的小说图像,如《武王伐纣书》中的“文王遇雷震子图”,《乐毅图七国》中的“鬼谷下山图”,《前汉书续集》“刘武刺汉王图”等,图像通过道教仪式的塑造,表现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其与佛教因果、儒教仁义相融合,带有鲜明的劝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相平话》道教仪式图像的构建中,丫鬟、奴仆、衙役、囚犯、兵卒、小民、幼童等形象被画工广泛编织于图像之中,实现宗教仪式场景的底层观看(如图9)。

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平话》
社会普罗大众的围观、直观、旁观、窥视形成插图的大众主体性,其与小说图像道教修辞符号形成视觉交换关系,最终形构世俗观看之眼中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色彩。
小说图像道教仪式体现仁义、劝善道德伦理,如葛兆光所说:“其与佛教中的因果轮回思想融会,与儒学中的伦理纲常结合,突出了道教中的鬼神迷信与宗教伦理成分,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特点,向民间渗透。”[14]
以上我们讨论了小说插图中的佛教、道教仪式景观,视觉图像反映的儒道佛观念并不是单一性质的,它是大众接受宗教折衷思想的体现。大众阶层建构的宗教信仰中,仪式是体现仁义、德行伦理教化的行为模式,其反映了底层百姓的宗教思维特征。儒道佛制度化宗教在底层的传播,与元代民间宗教的内核思想存在共性。
王铭铭认为:“中国民间宗教指的是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1)神、祖先、鬼的信仰;(2)宗庙、年祭和生命周期仪式;(3)血源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4)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15]
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道、佛、儒折衷形成的“亲亲”“孝悌”“仁爱”等教化思维,与民间宗教的神、祖先信仰、宗法秩序提倡的仁义礼制具有相同特征。《全相平话》宗教仪式图像表现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伦理观念,即是民众信仰神、祖先、鬼信仰仪式,以及伦理教化思维的象征。

《增订建阳刻书史》
由此可以看出,元刊《全相平话》宗教仪式图像折衷了儒道佛三家观念,反映了仁义、忠孝、劝善教化主题。小说图像仪式借助因果报应、善恶业报等宗教场景,构建了政教合一语境下的道德观念。
Daniel Stevenson认为:“在个体的修行中,这类仪式节目被看作是观行、观心之举不可或缺的补充。它们的特殊逻辑……预设了前世因果、善恶业报的观念,而对其特性须加以演述和处理,使其成为修行者训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说图像正是对元代建阳地区民间宗教劝善、仁义、孝悌的演述,其反映了大众伦理教化与信仰标准。[16]

五、伦理透视:儒道佛教义折衷与信仰生成
埃米尔·迪尔凯姆 ( E. Durkheim)曾提出“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组成的统一体系,……宗教实践是一种明确定义的强制性的行为方式,就像道德和法律的实践一样。”[17]作为中国本土制度化宗教,儒道佛在《全相平话》小说插图中表现出民间的宗教信仰与道德实践。

《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毫无疑问,小说图像中的宗教仪式有助于张扬宗教思想,天意改朝、神魔救难、地狱判案插图主旨以超越凡人能力的神化书写传播宗教的特异性。
那么,小说插图的语图叙事,为什么会表现出宗教折衷及德行教化的特征呢?元代建阳地区的宗教语境,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念,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元代建阳地区主要盛行儒释道三教,即以朱子理学为主的儒教,以临济宗为主的佛教,以清微派为主的道教。
建阳县三教势力强盛,当时建宁府管辖7县,设置的儒学书院共21所,每县平均3所,道家庙观共89所,每县平均12.71所,佛教寺庙共279所,每县平均39.86所,按照明代嘉靖《建阳县志》统计,元代建阳县有儒家书院16所、佛教寺院137座、道观55所,儒、道、佛机构在建宁府总数中占比分别为76%、49%、61%。
由此看出,元代建阳成为建宁府乃至于福建省重要的宗教活动区域,在儒道佛三教运动语境下,社会大众宗教活动较为复杂,民间的宗教信仰包含了诸种伦理因素。
一方面,受元代政府开放的宗教政策影响,儒道佛三教势力颇为壮观,而在宗族制、家长制为核心的大众群体中,儒教伦理秩序占据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元代制度化的宗教佛教、道教通过教义伦理掌控着和尚、道士的行为,但其无法像儒教一样影响世俗大众的社会行为。为适应社会大众需求,元代主流宗教不仅借鉴了儒教伦理中最具策略性的精华,而且不断与之相妥协,其形成的新的道德、伦理成为世俗大众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部分。

《书坊乡志》
小说宗教叙事图像不仅反映儒道佛宗教观念相互折衷,而且构成了社会伦理秩序规范与道德教化。
首先,在儒教层面,政府以儒学取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儒教立国对各地宗教起到规约与制衡。
元代建阳地区是朱子故里,《建阳县志》载:“及南宋朱熹、蔡元定诸君子倡明导学,彬彬然为道义之乡。”[18]朱子理学在建阳广泛传播,本地书坊如余氏勤有堂、刘氏日新堂、虞氏务本堂等,刊刻大量的理学书籍,宣贯儒教教义。
这些书籍在建阳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9]
《全相平话》图像所反应的“仁义”“忠信”“孝悌”儒教伦理,即是朱熹儒家教化的核心部分。朱熹提出的“阴阳五行之气,健顺五常之理”,核心在于“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全相三国志平话》
他承认道教阴阳五行之说,并上升为人性伦理的儒家纲常之道,朱氏佛、道神魔思想的儒家释义在建阳世俗社会形成风尚,“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本欲敦民俗而厚风化,必得行实卓越、节操超绝者,方可垂劝将来”。
在此语境中,“仁义”“忠孝”主旨在《全相平话》宗教图式中屡次出现,无论帝王、公爵、将相、士大夫等帝国权力,还是游侠、大盗、散客、平民等个体,儒教道统基于“仁义忠孝”的内核逻辑形构政教空间秩序。
其次,在佛教层面,建阳地区盛行的临济宗源于禅宗一脉,元朝政府在民间选取百寺用以传教、供佛,《闽中金石略》载:“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佛长明灯。”[20]
寺院僧人及信徒所传教的《华严经》《法华经》等,在于籍助善恶、轮回经书要旨宣扬仁义、善良德行,佛教徒刘谧云:“佛以五乘设教,……人乘者,一曰不杀、而曰不盗、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语、五曰不饮酒、六曰不两舌、七曰不恶口、八曰不嫉、九曰不恚、十曰不痴。兼修十善者,报之所以生天也。”[21]佛教徒从教义经典中总结的社会善意行为,与儒教的仁义道德是相同的。
最后,在道教层面,元代建阳人黄舜申创立的清微道派,其教义融合了禅宗“明心见性”与儒教“理气论”学说,并在民间产生较大影响。

《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
《清微斋法》指出:“道家之行持,即儒家格物之学也。盖行持以正心诚意为主,心不正则不足以感物,意不诚则不足以通神。”[22]
清微派融入儒、佛学说,在民间宣传劝善修身行为,并为百姓开展施符、驱邪、超度等宗教活动,亦是为强调道德秩序与仁义规范,正如黄舜申所云:“若习于善则此心广大光明,与天合德,是名白业;若习于恶则此心昏昧,惨塞同地卑污,是名黑业。”[23]
劝导百姓善良、讲求德行,这于儒教伦理规范相一致。也就是说,儒道佛制度化宗教虽然教义不同,但在仁义道德与伦理秩序方面存在相互趋同,底层大众基于朱子礼教观念,对佛教、道教的劝善、仁义等修行予以借鉴,最终形成了民间复杂的宗教信仰。
从宗教角度来看,元刊《全相平话》是建阳地区宗教文化书籍,其杂糅了大众关于儒道佛三教劝善、德行等道德伦理。
小说图像与文本符号共同展现出大众对于社会事件的评判标准,休谟指出:“在所有曾经信奉多神教的民族中,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24]

《建阳刻本书目辑要》
《全相平话》小说图像产生在元代,其时儒道佛等制度化宗教世俗化进程加快,小说插图不仅是宗教史演进的视觉展现,同时表现出大众对生活、人物、历史事件宗教观念。这种观念具有复杂的伦理构成和民俗信仰,其以儒家政教观念为基础,汲取了佛教、道教善良美德、仁义忠孝等伦理成分。
《全相平话》小说中的祭祀图、神仙图、斗法图等宗教图式,形成了一套“政教—德行”表意体系,其编撰反映出建阳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成。如小说图像中绘制了大量神仙人物,这些人物是民众信奉的天神,他们附加了宗教色彩,并带有固定的生成模式。
殷郊、雷震子、关羽、韩信、英布等均为天神下凡,画工以图像符号表现出宗教神在大众视域中的生成演变。
《武王伐纣书》太子殷郊为道教太岁神下凡,“有一日,姜皇后降生一太子,因王打泥神,天降此人,此人便是太岁也”。小说插图通过殷郊杯盏打妲己、山神庙获神斧、斩杀纣王妲己等神异事件的刻画,反映出底层大众神仙信仰的生成模式,即生为凡人、忠孝爱民、遭受厄运、斩妖除魔、信仰造神。而关于太岁神的角色绘制,则被画工绘制成普通的真人形象。
再如,原属于道教神系统的雷震子,小说文本绘制其肉翅、雷公嘴、黑面,而在小说图像中被绘制成穿盔甲的战士形象。画工将天神绘制成凡人形象,意在突出其人性面貌,殷郊、雷震子、关羽、韩信等人的事迹特征即是忠孝仁义、除暴安良、为民除害。

图10:《武王伐纣书》卷中“肉翅、雷公嘴”的雷震子形象
这类去神化图像实践,如《前汉书续集》“吕后祭汉王图”、《全相三国志平话》“天差仲相作阴君图”、《乐毅图齐国后集》“迷魂阵图”既拟仿“神灵助厄”“仙人赐物”“神魔斗法”神仙形象,又呈现图像符号对神仙的排斥。
海德格尔曾提出视觉主体性进步标识:“形而上学沉思者追问真理性,科学的发展,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成为体验对象,以及‘弃神’”。刊刻技艺发达的建阳书坊将图像符号应用于小说美学,反映了神化叙事弃神实践与儒家政教场域搭建,标志着儒家思想对视觉文化场的解构与约束。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图像中出现的太岁神殷交、雷神雷震子、关圣帝君关羽、地狱判官司马仲相等神仙角色,在《全相平话》中扮演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等天命事件的主导者,这类人物反映儒释道三教伦理价值观。

《全相三国志平话》
而图像中的天神故事,宋元之际流传于民间,并有着民间宗教的信仰体系。一方面,民众为他们设置庙宇祭祀,祈福避害,宣扬价值伦理。另一方面,民众对宗教信仰的价值标准存在着大众判断。
元代建阳县志载有神仙信仰的生成过程,如《陈录事庙》一则,叙述陈姓神仙庙宇的修建及祭祀原因,其信仰标准与《全相平话》中的神仙相一致。
旧志神姓陈讳岸,昔为邑录事,以直方清粹称,子三人俱以行义著。唐贞观中被谗,父子三人同时遇害,弃尸于溪,沂流而上数十里,时有范头陀者率乡人立庙以祀之。宋元丰中封威惠侯,……三子皆封侯,曰协义、曰协信、曰协济。……神屡恩助国难,恩泽惠民,民怀其德,为之立庙,累之为王室。[25]
材料中的陈氏家族,之所以被建阳民众供奉为神仙,是因为他们具有仁义孝悌、忠信重义、护国惠民的品行。
《建阳县志·秩祀志》言:“国之大事在祀,盖所以崇报萃涣,怀柔百神也。其在祭,仪法祀于民者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抵大患则祀之。”[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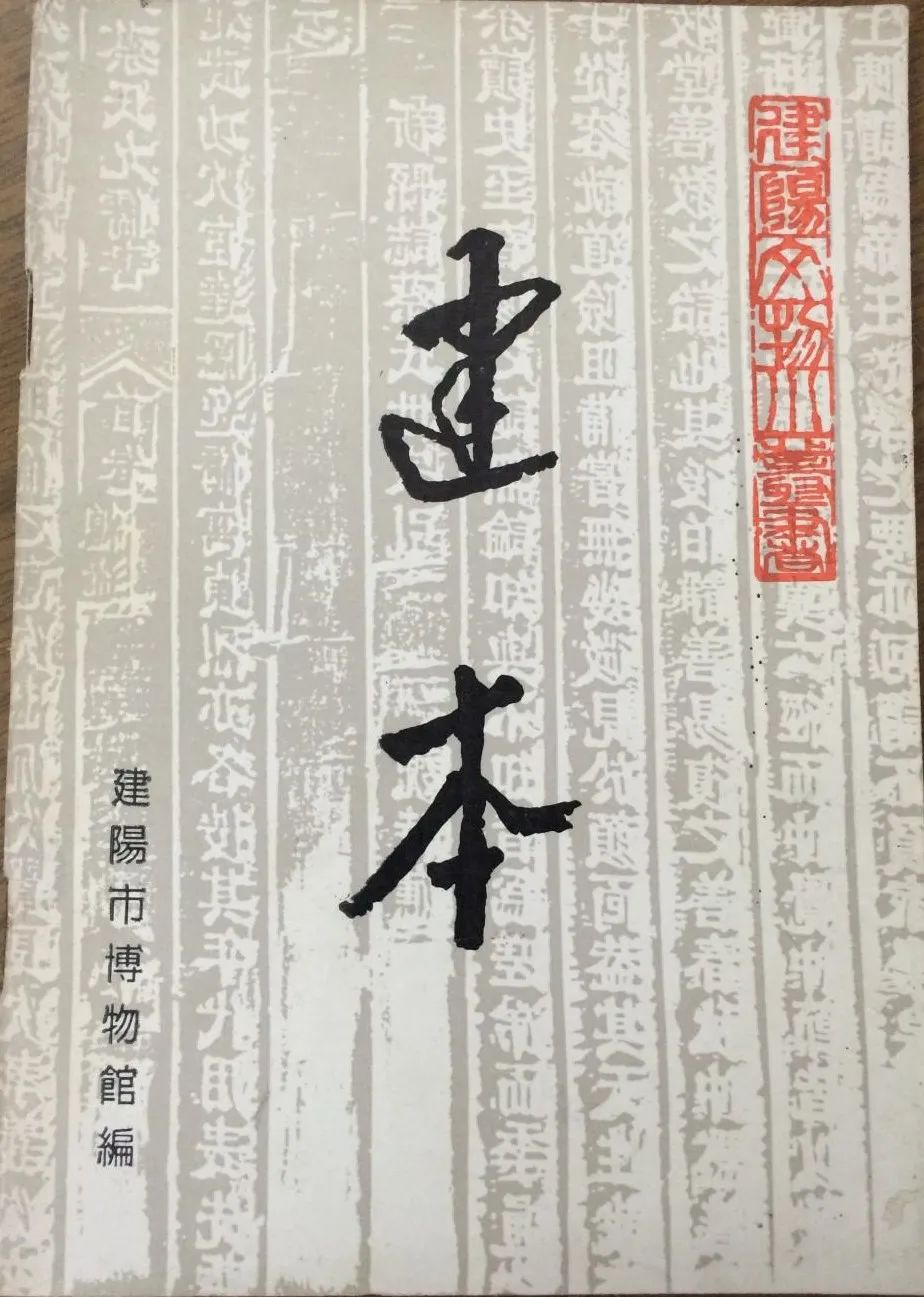
《建本》
也就是说,建阳民间宗教的信仰标准是神灵个体需要有政教仪法的代表性,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仁义道德示范功用,他们在护国爱民、崇德报功、教化民俗等方面具有典范价值。
这一点与《全相平话》小说图文关系蕴含的天命无常主题意志、儒家政教秩序观、儒道佛道德教义相同,小说民间宗教信仰的书写是对社会礼法、道德、秩序的全面彰显,表现在具体事件则为忠于君主、爱民如子、孝敬人伦、抵御灾害。
一旦神灵违背价值标准,则会为大众伦理批判。“闽人之赴花会者,必供一偶像于家,旦夕祈祷,以图默佑。胜则享酒醛牲牢之奉,若败,则泼以便溺,甚且痛詈而斵削之,或抉目,或劓鼻,或截腰,或斫手足,弃之于青,盖愤其无灵而虚享血食也。”[27]神灵护佑百姓则信奉,否则即会被销毁。
由此看出,《全相平话》图文关系反映的深层伦理,是建阳民间宗教信仰的价值体系,其存在儒家政教的功利特点,并与道教、佛教所形成的仁义、孝悌、忠信、爱民等伦理教化相勾连。

建阳书坊乡全景图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插图以天命无常宗教观为图像主旨,图像空间塑造了儒家政教秩序,小说图像通过宗教仪式的刻画,反映出元代大众对儒道佛仁义、孝悌、忠信、善良道德的综合接受,其表现的信仰价值体系包含着儒家政教伦理及三教折衷教化观念。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插图本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第一个视觉文本,插图作者吴俊甫、黄叔安来自社会底层,其版画创作具有大众代表性和民间宗教文献价值。
相对比稍晚的《西游记》《水浒传》等建阳出版的小说叙事版画,《全相平话》具有复杂的宗教文化艺术形态,其是儒道佛世俗化进程中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与佛道兼容的特征。

《明代建阳书坊牌记考释》
我们认为,小说插图通过对儒道佛三教形象的刻画和形态展呈,直观反映了元代社会宗教的内在道德伦理与信仰标准。
注释:[1] 本文所探讨的元代制度化宗教,指的是儒、道、佛官方认可的宗教,相关界定,参照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籍。
[2]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全相平话五种》小说插图叙事展开,如张晓娜《全相平话五种》版画图像研究(2022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李彦峰《论元代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文图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此类研究基于“语图关系”,探讨小说图像的叙事功用。
[3]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4] 本表依据《全相平话五种》小说插图中有关佛教、道教神魔叙事展开,部分插图意义表征较为隐晦,笔者根据文本叙事中的神化情节对应罗列,凡没有神魔书写场景则不予列入。
[5] Karl Kurger:“Concluding Remarks on Two Aspects ofthe Chinese Unitary State as Compared with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ed.S.R.Schram,Foundatiom attd Limi“of State Power in China(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104.
[6] 范丽珠、程娜:《论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的耦合关系:中华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理论建构之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7] 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周秋良译:《迪尔凯姆论宗教》,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8] A.F.C.Wallace,Religion:An Anthropology View,1966,PP.75—76.
[9] 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 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6。
[10] 戴森:《元代宗教戏剧世俗化特征论略》,《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第75页。
[11] 黄元吉:《净明忠孝全书》卷4,《道藏》第24册,第36页。
[12] 纪霖、宋宏编:《史华兹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13] Mark Meulenbeld, Demonic Warfare: Daoism, Territorial Net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a Ming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5。
[14]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
[15]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
[16] Daniel Stevenson:“Buddhist Ritual in the Song,” pp. 340-341。
[17] 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周秋良等译.《迪尔凯姆论宗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18] 冯继科:《建阳县志》卷三,第36页,明嘉靖刻本。
[19] 朱熹:《朱子文集》卷10,《建阳县学藏书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7页。
[20] 陈菜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一,《佰大寺看经记》,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211页。
[21] [日]高楠顺次郎:《大正藏》第52卷,《三教平心论》卷上,第781页。
[22] 任自垣:《道藏》第4册,第286页,明永乐刊本。
[23] 任自垣:《道藏》第4册,第286页,明永乐刊本。
[24] 休谟:《宗教的自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5] 冯继科:《建阳县志》卷五,第93页,明嘉靖刻本。
[26] 冯继科:《建阳县志》卷五,第76页,明嘉靖刻本。
[27]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