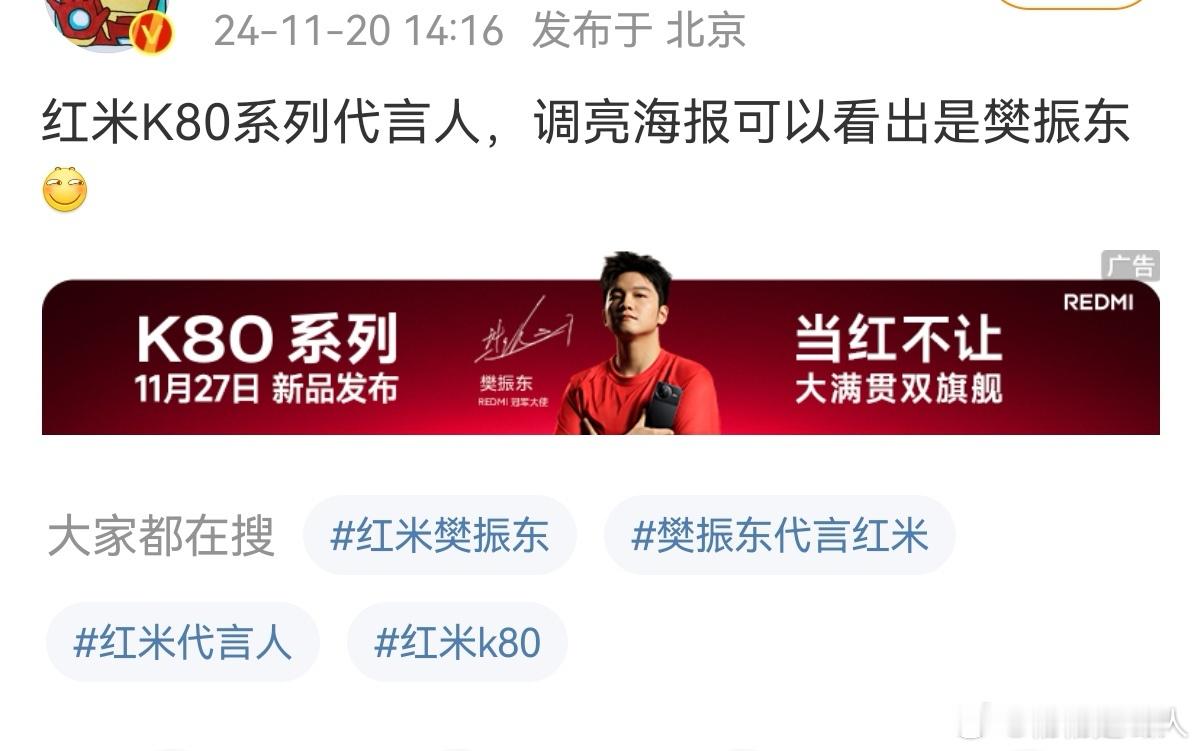简介:
这是一个闲来无事,幻想的故事。
其中没有主角,每一章是单个人物的视角,以此拼凑整个故事。起初因为好玩这样写,如果令人读起来费力,那应该是我技巧的问题。
内容没什么特别。我觉得喜欢历史,感受力强的人会有耐心读下去。
希望快点写完,希望我的脑力够用。

精选片段:
南岭的清晨总是弥漫着雾。在我失眠的无数个夜晚,总是默默望着红日从远处的山后升起。那时天色一片淡红,雾气像轻纱一样,翻腾着渐渐散去。接着就能看见大片芭蕉叶,还有许多玲珑剔透的水珠,从叶尖滴滴答答掉在地上。那声音真像安魂曲,终于我可以安心睡去。
黑夜过去,我的心魔已消。朦朦胧胧中有侍女的绵言细语,或是那个凶神恶煞的老头在窗外狠狠扫着落叶。我可以睡得更安稳了。其实我并不怕黑夜,也不想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我只是害怕控制不了的事物,未知的人和事总让我禁不住遐想联翩,而依据自己的处境或是自己的本性,那些臆想总是带来最坏的结果。
母亲对我严厉却体贴。比如她知道我失眠的习惯,清晨时分总会静静在坐在一旁,低头做着每日的针线活。一个时辰后,就有双坚定的手推我起床。我熟睡的时间也只要一个时辰。
每日母亲都要去马厩,她去马厩时总是把头发挽成一个总髻,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然后套一件白色长褂,再用草皮把鞋裹起来,用绳子也捆得严严实实。
母亲走后,留下我对窗临字。每天上午我也有繁重的作业,就是把母亲留在案上的书背熟背滥,将她圈起来的文章临摹几遍。有时我两眼茫茫,不知道这种意气用事的努力是否值得。但是为了母亲,她说什么我都会照做。
中午母亲就回来了,我也把功课做好。这时会来两个侍女,一个打扫屋子,一个替我们做饭。我们毕竟是皇族身份,只要把奴隶的活干完,就可以享受贵族待遇了。当时南岭的国君曾命母亲做惠公主的音律老师,母亲的琴艺早已扬名内外,南岭人喜好音乐,所以国君也对母亲分外礼遇。可是母亲在朝殿上把头一扭,她不答应。南岭的君主笑了一笑:“那么还有两份差使。洗衣和喂马,常夫人挑一个吧。你们在南岭的漫漫岁月,总不能白吃白住。”
于是母亲去伺候马了,她情愿伺候马,也不愿伺候人。不过马在南岭的地位仅次于人。我长大后常想,这是一个多么贪图享乐的民族,只要在峻岭中找到一块绿茵地,他们就围起来赛马射箭。白天马啸嗷嗷,晚上乐吟细细。而中丘就这样被他们打败了,也许元相带着十几个智囊在夜灯下苦思飞山越野的连环计时,他们已一路凯歌攻破城门。
父皇那年惊慌失措的表情我记忆犹新。
“你们——”他一手持剑,一手指着那些闯入者。两个武将把他拖到一边,用刀架住他脖子,对面的角落里,畏缩着母亲和我。我们看着流烟滚滚,碎石一地。国库被撬开了,华光流彩一泄而出。那些盔甲兵蠢蠢欲动,就是棋盘上东张西望,不安分的卒。父皇知道祠堂被烧后晕在了地上,这时庄太师踱步进来了,他扶起倒在地上的父皇,对着乱窜的盔甲兵说:“你们谁都别动。”结果真的谁都不动了,有人朝祠堂泼了几桶水灭火,后来父亲就醒了。
母亲和我依旧畏缩于角落,睁大眼睛看了这一幕,母亲的指甲掐进我的胳膊,我们一起感到了痛。
庄太师是南岭的国师。他在中丘出生,父亲是陶器商人,母亲是南岭的皇戚。他在少年时代迁徙南岭,在母舅家中长大。他聪敏好学,过目不忘,又常在春秋二季的狩猎赛中争强好胜,那时的老君主说:“真是匹犟马。”后来命他管理南岭散兵。他身上有南岭人的骁勇善战,也遗留了中丘的自律严谨,二合为一,在应付中丘的屡次战役中得心应手。老君主仙逝那年,就把幼主托付给他。
此时庄太师再次回到中丘,却打开了天子大门。他对中丘臣民十分客气,似乎念着故情,一把将父皇扶回了龙椅。
“老亲家,别伤心,你祖宗的东西都还在。”中丘与南岭几年交好几年交恶,中间还有几次姻亲往来。所以太师一开口就叫亲家。
父皇抱着几尊凄惨惨的牌位并不领情。太师说什么他就是木然呆坐,不言不语。我那时才十岁,本来兵临城下千钧一发,可突然来了一位白发老翁,慈眉善目地将枪剑挡去,我又惊又喜,几乎把敌人当作恩人来感激。
南岭军队在皇城驻军百天后撤离,这一百天让父皇老了十年。我那时懵懵懂懂,依旧在皇宫中玩耍嬉戏。直到走的那天,那位白发老翁将我抱起,我这才看清,那对藏在白眉与细纹间的眼睛有多么犀利。
“太子殿下,随老夫去南岭玩几天好嘛?”
我回头看着父皇,父皇却转开了目光。母亲却走过来,冷静地说:“带我一起走。”父皇似乎摇摇欲坠,挪开嘴唇想说什么,可终究没有出声。太师哈哈一笑:“那请夫人也一起上路吧。”
就这样母亲和我来到了南岭,春去秋来,已经整整八年过去。
伺候我们的侍女永远是她们两个。下颌很宽,身材微肿的叫秋实,另一个眼下有颗痣,走路很妖娆,名字叫春叶。她们都不和我说话,似幽灵般飘来荡去。我初到的几月受惊过度,晚上总是尿床。第二日春叶掀开被子,就捏着鼻子叫:“啊呀——”几次后,她就特别怨恨我,偶尔瞟我一眼,连带那颗痣都会扭动着表示它也恨我。
相比之下秋实为人敦厚多了。我从炼房出来后,浑身脱水,脚尖打颤。母亲作势教训了我几句,转身时却偷偷拭泪。那日晚上秋实做了鲫鱼汤,拍着我的背,一勺勺喂进去。第二天吃小羊腿喝羊奶,第三天吃稠稠的糯米糕,吃得我以为又回到了中丘,我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子。可等我身体好了后向她道谢,她又板起脸,突着下颌吓唬人,仿佛前几天的事不是她做的一样。
我们在南岭的生活如隐士般销声匿迹,因为已没人需要我们。南岭拿到了他们要的东西,五座城池和背后连绵的煤矿,他们还强势驻军位于交界线的邺城,将中丘百姓渐渐迁走。而父皇呢,我们被软禁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我的叔父登基,当然是经过南岭朝廷点头的。无人来请旨将我索回,当然南岭也无人送我回去。到此,我真成了遗世孤鸟,生死无人问津了。
这段灰暗的成长期让我变得沉默寡言。母亲总是让我读很多书,读得我头痛欲裂。只有午后的两个时辰是舒畅的,我可以同游栗骑马游猎,可以摆脱四周如鬼魅般的监视。我发觉自己并无舞刀弄剑的天赋,站在身型练达的南岭男子中间好像一个乔装改扮的女人。好在我的射术不错,又喜欢骑马,这几年总算把微驼的背挺直了。有一年除夕,南岭王一定要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个杂技,我拿着弓对准靶心,却一箭射死了一旁乱吠的狗。那是惠公主的爱犬,她当即哭闹不休,一定拿箭射死我。那帮小人为寻开心,就把我捆在柱子上。公主根本拉不开弓,换了好几副,才眯着眼瞄准我的脸。我似乎听到母亲在一旁重重的呼吸声,游栗紧握的拳头咯吱作响。结果,第一箭只射到半程就掉下来。她又拔出第二支,恰好侍郎的公子在一旁,笑眯眯说:“公主,把胳膊抬高点,这样才使得上力气。”他刚要伸手靠近,那惠公主就翻脸骂道:“滚,离我远点。”
那时满朝文武似乎都在议事,无人关心公主的射术。惠公主是南岭王的掌上明珠,也是我在南岭见过最漂亮的少女,乍看之下我见忧怜,谁也不忍心去伤她半毫。可她瞄准我时,漆黑的眼珠四下一溜,像只狡猾的狐狸。
小狐狸终于放了弓箭,蹦到了我的面前。她拿弓提起我的下颚,轻巧说道:“以后你就做我的人靶子,等着我一箭射掉你的眼珠子。”我只好回答:“公主,以你的资质,还要好好练习。”
她像是吃了一惊,转而又笑道:“做囚犯还这么嚣张,难怪父王说你戾气未除。拿镜子照照自己,多像山谷里夜行的饿狼。还有啊,今天你杀了我的狗,我也要杀了你的。”
我心想我哪有养狗,她却一侧身,对不远处的游栗叫道:“你过来!”
游栗立刻大步上来,像鼓起帆的战船一般,还不等公主发话,就铿锵有力地训斥公主:“你已绑了我家公子多时,公主请别得寸进尺。要是公子有半分差池,游栗都不会放过他,不论她是谁。”
她大概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囚犯的随从大声斥责,一时怒意从眼里溢出,一扬手就要打人。谁知游栗更快捉住了她的手,使劲一捏,就咯咯作响。
这下举座皆惊,君主更是站了起来。
母亲立刻从人群中站出,轻声喝止:“栗儿,放了公主。”
他对母亲从来毕恭毕敬,旋即松手。公主退了两步,像是对他很害怕。
游栗知道闯了祸,需要平息全场怒火,他朝公主跪去,看了我一眼,慢慢垂下头。
南岭有一个惩罚重犯的炼房。我初到南岭时,被一群年过半百的阉人私下关了七天。因为南岭君主和庄太师都反感阉人,登基后就皇宫就不再招纳男童,所以宫内能看见的都是前朝留下的遗臣。我常被这些人欺负,他们被新君主嫌弃,一腔怨气无处发泄。而当时我还不经世事,以为自己还是矜贵的太子爷,见了母亲被讥讽,或是游栗被虐打,往往控制不了脾气。一日就朝他们中的某个一脚踹去,结果就被关了进去。
七天里我蜷缩在一个四面是墙的狭小暗格里,墙角有一个漏隙,偶尔会冒出馊水的味来。我不敢睡觉,闭上眼睛就有幻觉,仿佛总有只手按住后脑勺。每晚他们都把我拖出来,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不敢在白天用刑,司刑官并不知道关了一个我;也不敢用铁铐火烙那类刑具,怕留了痕迹被人发现。他们打完我后就吓唬我,说要把我也阉了,阉掉后就能伺候他们。中丘的太子变成阉人,这想法让他们都哈哈大笑。我当时蹲在地上,四周变态的笑声和漫无止境的黑变成我一生的梦魇,从此我只在有光的地方才能睡。
游栗步我后尘,为了惩罚他折断公主的手,君主命他去炼房受刑。当年父皇命他保护我,陪伴我在南岭的日子。无论父皇还是我,谁都没问过他是否愿意。我会这么想是在经历了种种屈辱后,在我体内的皇族血统已无法使我感到骄傲后,我不再把任何人看作自己的仆人,有义务陪同我在南岭受苦。
他被人打掉半条命,扔在母亲的院子口。几天后庄太师叫人送了人参来,还有一些药材和香米。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直无法理解这个人。他将我困在南岭这么多年,不让我干脆死去,也不以我去要挟中丘再图利益。他似乎把我们忘了,可他又送了人参来表示他的善意。母亲认为他城府太深,认为他是中丘复国的大患,他有任何举动都会惹得母亲费神揣测半天。多年后他简简单单地死去,未有任何异动,未有任何遗言,害得母亲寂寞了好一阵子。
游栗捡回一条命,除夕过后一直躺在床上养伤。那年冬天下了好多雪,从窗户眺望,远处的山峦都是连绵起伏的白色。游栗没法出门,被关在的院落里,整天拿着小刀削木头。后来惠公主来了,她总能为我们带来许多麻烦,那几年我非常讨厌她,她公主的身份总是提醒着我曾是个太子。
惠公主的右手腕被石板固定着,左手拿了跟银质鞭子。她头一次来,模样真不好看。我当然知道她是个美人,可我不喜欢被娇纵的美人。她的疾言厉色吓不倒我,还有仗着一点小聪明的撒娇痴缠,以及得逞后的得意样,也没让我同其他皇孙公子那样意乱情迷。
“喂——”她一来就把两扇摇摇欲坠的木窗捅开,然后探进半个身子。那天下着小雪,她骑装的领口绣了许多梨花,呵一口气,空气里都是清香。
“喂,跟我们一起玩?”
门外十分热闹,公主的亲卫队个个裘衣皮靴,冰天雪地里开得姹紫嫣红。
我头也不抬,把书抓得很牢。
“你不去,那就他去。”她瞥一眼游栗,“他不是很喜欢替你出头嘛?力气又大,嗓门也大,等一下放点血,扔进猎场,好把野熊都引出来。”
她朝随从使了眼色,有人要来架走游栗。我站起来挡在门口,真想把这个女的扔出去。
“我去,游栗留下。”
公主听了后,转身就走。哪知游栗摇晃几步,紧跟我们身后。公主回头,他走上来同我说: “公子,这姑娘心肠狠毒,让我跟着你。”
公主嫣然一笑,说:“那好,一起走吧。”
在我能够回忆的儿时片断里,公主总是一个鲜明的存在。她的存在会把许多事都勾勒出来,让我不至于因为太老,或是太敷衍时间,而忘记很久以前的自己。
那天发生的事有点险象环生。公主坐一辆宝石蓝的小马车,她的落云——一匹喜欢撅臀伸脖子,总是迷路的白马——不习惯拉车那么重的活,跑几步就要歇一下。几批狩猎的马队都跑到前面去了,只留了四五个随从跟着我们的马车。我坐在前面赶车,公主和游栗坐在后面。她时不时在山谷间响起嘹亮的口哨,那时未去过冬的灵鹊便三五成群,绕我们的车顶盘旋。
公主问游栗:“要是不困在南岭,你会做什么?”
游栗说他会行走江湖,做一名的侠客,多半被官府通缉,却有很多女子倾慕,听得公主咯咯直笑。接着她说她要做女巫,最好是又漂亮巫术又高,住在一辆宝蓝色的马车里。
游栗就说:“有一天侠客受了伤,就逃到女巫车里——像现在这样。没想到女巫蛇蝎心肠,驾着马车把重伤的侠客给出卖了。”
“呸!”然后公主挪动了一下,该是坐到游栗身边。这时马车颠了好几下,在砾石路上咯吱咯吱地前行,使我听不清身后的对话。
等我听得清楚时,公主在说:“你家公子不爱说话,脾气又犟。我们头一回见面,我送他一口袋苹果,他都扔地上了。”
游栗回答:“那时他还小,也不喜欢吃苹果。如今你再送一遍,他就不会扔了。”
“我不信。”
车里静默,我感觉背后有束凝视的目光,许久公主又说:“你跟了他这么久,都不了解他。”
游栗没有争辩,大概他在盘算等一会到了猎场,怎么在一大群野熊里抽身而退。这时公主又用她一贯动人的嗓音娇笑道:“你生气的样子也挺像野兽的,等会儿披块熊皮,把你跟真的熊关在一起角斗。你说好不好玩?”
她又是嬉笑又是恐吓,把游栗惹得心烦意乱。他一把甩开她,爬到前座来。
“我真想把她那只手也拗断了。”
“然后塞进她嘴里。”我补充道。结果游栗大笑起来,把公主招来的灵鹊吓得惊飞四散。
后来我坐在中丘冬日的阳光下,想到那个下午也会笑。只可惜没有玄冰,要是玄冰也在,那个画面就完美了。我或许会驾着那辆马车,一直走到人生尽头。
结果是我们的马车遭到一群狼的攻击。游栗最先听到声音,可不相信野狼会在白天这么出动,我们依旧悠闲前进。直到公主叫了一声,才发现右边山间隐隐约约都是狼头。大概是饿了一个冬天,实在忍不住了。我们身后只跟了四个随从,一辆货车,面面向觑,人和马都惊慌失措。
“公主,小白马跑不快,要换侍卫的马我们才能逃脱。”我朝后面喊,“你们都上车,把马拉过来。”
可公主叫得更大声:“不行!它跑不快,会被狼吃了。”这幅情景她忍受不了,光是想想,就叫她两眼通红。
游栗说:“那我们分开跑,都上马。”公主一只手还被石板夹着,另一只握着缰绳。我拆了拉货车的两匹黑马,同游栗一人一骑,将公主夹在中间。我对游栗笑道:“终于有机会打这头畜生了。”游栗回头一望,高喊:“狼来了,跑吧。”然后一扬鞭,重重抽在落云的屁股上。
南岭的君主是个微胖的,永远用温润嗓音同你说话的中年男子,同时也是疼爱女儿的父亲。公主被送进宫那刻,他脸上有片刻焦虑的神色,似乎不耐烦地朝游栗同我瞅了一眼。不过后来大臣们愤愤指责我们时,他又说了公道话:
“是惠惠强迫他俩跟去的,还拖累他们也受了伤。”
他不是真正的宽宏大量,只是惯性地平息朝堂上的矛盾争端,就像他平息朝政中的分歧一样。几年前他听从一位堂王叔的政见,要在中丘各省设督检司,管理各地驻军。后来督检司的府邸造好,驻军统领的名册也誊录,却被庄太师一一指出弊端,要进驻的军队三天内撤回来。那位王爷和庄太师在朝堂上互相指责,那时我也在那里,堂王叔特地请我来支持他的政见。
“现在中丘各地流寇四串,您的叔父管不了。那些暴徒进了监狱也不服管教,不把几千兵压在那里,他们就有胆子把衙门烧了。不知道老头吃错了什么药,我们养得兵强马壮,他不用来打仗却圈起来耍马戏。”
庄太师没有管我,只对王爷笑道:“你门下的那些人,到了那里只有坏事。一群羊会听一头狼的号令嘛?它们只会逃跑。那些门客跟了你许多年,是该喂个肥差犒劳,但是你要记得,别喂不属于你的肉。”
他们争执是常有的事,我通常沉默以对。目光偶尔掠过君主,他往往垂眼听着,有时摸一摸自己的袖子。我那时讶异他的宽容忍让,等他们争执完了后,他还两处安抚了一番。现在回想起来,毋宁说是他的好脾气,不如说是他两处都不关心。他被当作帝王培养长大,坐在龙椅上是他的责任。可他也有自己享乐的权利,等待戏班开锣的那刻,或是西泽的蛇女前来献舞,他的脸要比在朝堂上生动得多。
无论如何,这些品质足够他做一位仁君了。得知游栗命在旦夕,他还送了一根野山参。大概公主的花言巧语唬动了他,让他相信游栗只是个被迫困在异乡,却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奴仆。他的改观救了游栗一命,至少御医能时常过来看看游栗。游栗康复后,我俩亲自去谢过他。当时他和几个子女在谈论桌上的新鲜乳酪,惠公主提醒了他,他的记性不错,毫不吝啬地夸奖了游栗一番。我俩退了出来,世上是有那么些人,他的赞美或苛责都没法让你激动。
从此公主就以游栗的救命恩人自居。那天我引开狼群,一人往平地上跑。游栗和公主原本预备进树林,谁知游栗旧伤发作,从马上跌下来。公主一手握缰绳,另一只断手抓着他的胳膊,在狼口下救了他一命。后来御医还是把她的右手治好了,但是御医也叮咛她将来不能使力用右手。她听了后大哭起来,简直是大哭大闹,用力蹬脚,拿左手摔东西,好补偿她不能使力的右手。
宫里人人都迁就她。她本来就是南岭王最得意的女儿,如今更是侍奉她跟女神一般。我让游栗别太内疚,公主即使残废了,也会有人照顾得妥妥当当。
可是游栗心情大受影响。大概他情愿把右手赔给她,也不愿欠她的情。那天他俩浑身血淋淋,被赶来的马队救了,游栗已晕过去,公主瞅了我一眼,也被老麽麽抱走。等到我被传进宫,她已包扎梳洗好,坐在君主身边。
她把一切都跟父王说了,说几句还会拿父王的袖子擦一下眼泪,好像惊魂未定。除了最后,她把自己同游栗交换了位置。游栗骑着落云拖着她,身后还有一头凶悍的狼,怎么赶都不走,把他俩都咬伤了。
整个过程她都未看过我。当天许多人看着她带我们出来,可树林的事只有我们三个知道。没有人有疑问,可是四周奇异的空气暗涌,他们的公主把他们都赶走,却和两个别国的人质一起逃往。
我只能承认从那以后我不怎么讨厌她了,甚至还期望她来看我们。而游栗的心情则更明显,她不仅救了他还替他善后。他不能坦诚地表达感激,又不能洒脱地忘记。每次门前有马蹄声,他都会朝门口望去。
一日深夜,院里突然有轻微的脚步声。此刻已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只有我比白日更为敏锐,隐约有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果然有人进来,我按住被褥下的刀柄。那人动作很快,一手捂住我的嘴,另一手便举剑挥来。我双目一睁,月色正好反射在刀刃上,霎时间杀气腾腾。那人未料我醒着,一时分神,手上片刻迟疑。我已一脚踢去,同时看清门口还有一人,我立刻将身边的那人反按在床上,手上的短刀朝他脖子抹去。
那人动了一下就没气了。我朝门口看去,另一人已冷静下来,举起剑朝我背后刺来。他动作麻利,看来是训练过的杀手。我朝右一晃,剑还是刺中胳膊。那人几步便将我逼到墙角,见我退无可退,又是一剑刺来。这一剑又凶又猛,我躲闪不及,只好用手紧握住刺来的刀刃。那刀口离我的脖子只半寸,我握刀的右臂亦抬不起来反抗。正僵持时,门口又来一人,我喘着气,朝来人冷冷望去,心想今晚若是性命不保,南岭会如何公告天下。那刻心里竟有一丝凄凉的快意,好似雪山迷路的猎人等来了他的结局。
来人举起地上的四方凳子,一下就把我面前的刺客给打晕了。
原来游栗被我屋里响动吵醒,便过来看看。我示意他不要声张,又忙去母亲屋里察看。母亲正睡得安稳,我们就悄悄退出来。他把一具尸体埋了,另一个就捆在后院的煤窖里。此刻天已微明,我俩坐在窗下,一边清洗伤口,一边忖度是谁要我的性命。
游栗自然说是南岭的国君。南岭的国君,我心里想,他若要杀我,会巧立名目给我按个罪名,把我捆去斩首。暗夜杀手不是他的作风。或是朝中哪个官员,与中丘的皇族有仇,想暗中取我的性命。可他们等得也太久了。我们想了一番也无结论,只好等后院的活口醒来再盘问。
母亲知道后,同我们一起到了后院查看那杀手。他衣着普通,身上也无任何随带品证明身份。游栗盘问他多时,他显然为保性命,不作强硬的姿态,可兜兜转转几句,也说不出是受谁指令,只是一问三不知。母亲担心我的安危,命游栗这些天不可离开我。此刻天已大亮,到了她去马厩的时辰,她将一屋狼藉收拾了,又嘱咐我好些话才离开。
我带着游栗又回到煤窖,我不再与他周旋,命游栗把他两手按在桌上。那人见我神情冷冽,怕是有番酷刑,呼吸渐重。
“你别紧张。”我说,“我们现在做问答游戏。游戏规定我问你答,你要是故意答错,或是答不知道,就得受罚。受罚的就是你的手。”我敲敲他摊在桌面的十根手指,“你看每根手指都分上下两截,一次砍一截,你就有二十次机会。当然,要是超过二十次,就剁掉整只手,明白嘛?”
那人还是说:“我只是受命于他人,太子请体谅。”
他把太子叫得如此顺口,我心中疑云翻腾,问他:“你家乡何处?”
他只停顿一刻,便答:“邺城。”
我朝他脸上看去,笑道:“你不是邺城人。”
他还未作反应,游栗已手起刀落,一截小指滚落到脚边,我拣起来放回桌上。
那人压着嗓子发出一阵呻吟,以武士来说,他实在太不中用。游栗见他不停扭动,便拖着他的腿想捆去房柱上。谁知拖到一半,他两腿的绳子尚未帮好,惠公主突然推门进来。
游栗同我都是一愣,我脑中顿时转过千百个念头,如何遮掩此事。谁知那刺客趁着我们恍神片刻,已几步冲到门口,一把扣住公主的脖子,恶狠狠地朝我们说:“把马牵来。”
游栗示意公主别怕,对刺客说:“后院就有马,你放了她。”
公主何曾受过这种待遇,愤怒多过害怕,跺着脚说:“你反了?敢挟持我!”
那刺客反而扣得更紧,公主脸色发青,整个人几乎被他提到空中。
我已知道他不是南岭派来的刺客,就告诉他:“你走吧,趁没人发现。不过别弄伤她,否则你就走不成了。”
游栗已牵马过来。那刺客将信将疑,拖着公主挡在身前,生怕我们出尔反尔。
“别往西,今天骑兵操练。上马吧。”游栗把缰绳扔给他。
哪知他一松开公主,公主踉跄几步,站稳后,回身一个巴掌扇去。
“谁叫你们姑息这些草莽流寇,不准放了他!”
她那么发号施令,游栗同刺客又打斗起来。刺客显然恼羞成怒,下手狠辣。公主今日偷偷前来,也未带随从。游栗很多时候要顾着公主和我,束手束脚,那刺客看准机会,也不恋战,跨上马飞奔而去。
公主走到我身边,问我:“那是谁?”
那两个从天而降的刺客打碎了我苟且偷生的处境。我在黑夜里睁着眼睛,思索下半生该如何度过。我对中丘的皇位早已没了企图,叔父的模样都记不清了,他何苦派人来赶尽杀绝。现在我该如何做?深夜我望着星空,连挪动一下的欲望都没有。一个人果然不能有太多时间胡思乱想,他越想越多,就越干越少。这是庄太师消磨我斗志的手腕吗?让我适应南岭潮湿的泥土,温润的空气,还有大片桃花盛开的山涧。让我眷恋这种暧昧的粉红色,连做人质也能做出病态的快感来。
惠公主未将这事宣扬,我十分感激她。这种感激一直存在着,以至她再次捅开我的木窗,叫我一起去玩时,我不知怎么拒绝她。她的玩伴包括:南岭的侍郎公子,王妃的两个子侄,大盐商王瑞通的儿子。侍郎公子天生一副口才,对人情事故敏锐通达,他不露痕迹化解王九少对我的敌意,镇定自若,左右逢源,我没有抬脚而去多数归功于他。九少爷是王家独子,他父亲是管理南岭王宫吃食的总采办,也是富甲一方的盐商,占了南岭一半的盐仓。我常常奇怪他为何要跟着我们出游,因为他对一切都看不上眼。当然他是倾慕公主的,可没超过倾慕他自己。相比之下公主的两个表弟就和气很多。他们是一对双胞胎,长得文秀,笑容也文雅,总穿宝蓝色镶金线的缎袄,摆在公主两侧,就像两只一模一样的椅垫。
我渐渐明白为何公主喜欢纠缠游栗和我。她虽然讨厌这些人,却喜欢看他们为她争风吃醋,好为波澜不惊的生活做调剂。她生来什么都有,却成了她生命无趣的根源。平心而论,如果我同她对换位置,我会更离经叛道地去填充自己的人生。
所以每每九少含沙射影讥讽中丘男子时,公主就会适时来挑拨:“你们这些莽夫,怎么懂得欣赏玉器呢?”她会更靠近我一点,还狡黠地眨了眼睛。
结果九少更不屑,对我笑道:“讲到玉器,我父亲最近弄了一套白玉,总共六枚印章,都是似模似样的麒麟兽,由大到小排列,虽然每只不同,挨在一起却是玲珑各态,仿佛能动一般。我家的几位姨娘都感叹,凭她们那副好耐心,也做不出那么活现的手艺来。”
我答道:“这是羊脂玉做的,找来时不带一丝瑕疵。兽头的眼珠都是琥珀石,每只深浅不同。晚上熄了灯,摆在月亮下很漂亮。”
“确实漂亮,不亲眼见到我也不信。可惜这些东西不能吃也不能玩,没有半点实际用处。”九少笑道,“你父王老被这些东西熏着,玩物丧志,难怪丢了江山。”
“哎哟——”双胞胎齐声叫起来,“原来还是公子家的东西。”
中丘的赤印,一共六枚,对应六级等阶。朝廷颁令时,父王都要用相应赤印下印,每份政令右下方都有一块赤色图腾。我小时候老把那枚最大的麒麟兽含在嘴里,父王怕我咬坏了牙,就把不常用的都藏起来。有一年要处决一批死囚,他一时找不到那枚最大的,就把他们都改成流放了。
中丘破国的时候,那批赤印就没了踪影。如今竟然流落到王瑞通家里,不知道那颗为首的仁兽身上,还有没有我的牙印。
公主总要时时刻刻折辱我,她对侍郎笑道:“什么好东西,去拿来看看。”
侍郎对我说:“这也算一件宝物。可惜我们南国人不好此道,若是太师得了,他定会还给公子。不过现在留在九少家也是好事,世伯是个风雅人,总会好好保存这些印章。”
公主便瞅着王九少。
那一个想是很得意,语调也尖锐起来:“我爹爹收了几天,就分给几个姨娘了。她们要是拿来玩,就不知会扔去哪里,要一枚枚收回来可费事。”
其实我并不想拿回来。我在南岭待久了,这种泼墨画似的生活,粗线条的墨汁随意四散,让我同这些人一样,早忘了该怎么欣赏六枚宝贝。
公主凑近我的脸轻声道:“要是你想要回那些石头,今后就要听我的。”她的几缕淡发碰到了我的鼻尖,我被迫着朝后仰。拉开一段距离后,才看清她眼里的促狭,简直在幸灾乐祸地闪动。我又被迫掉过头去,掩饰嘴角的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