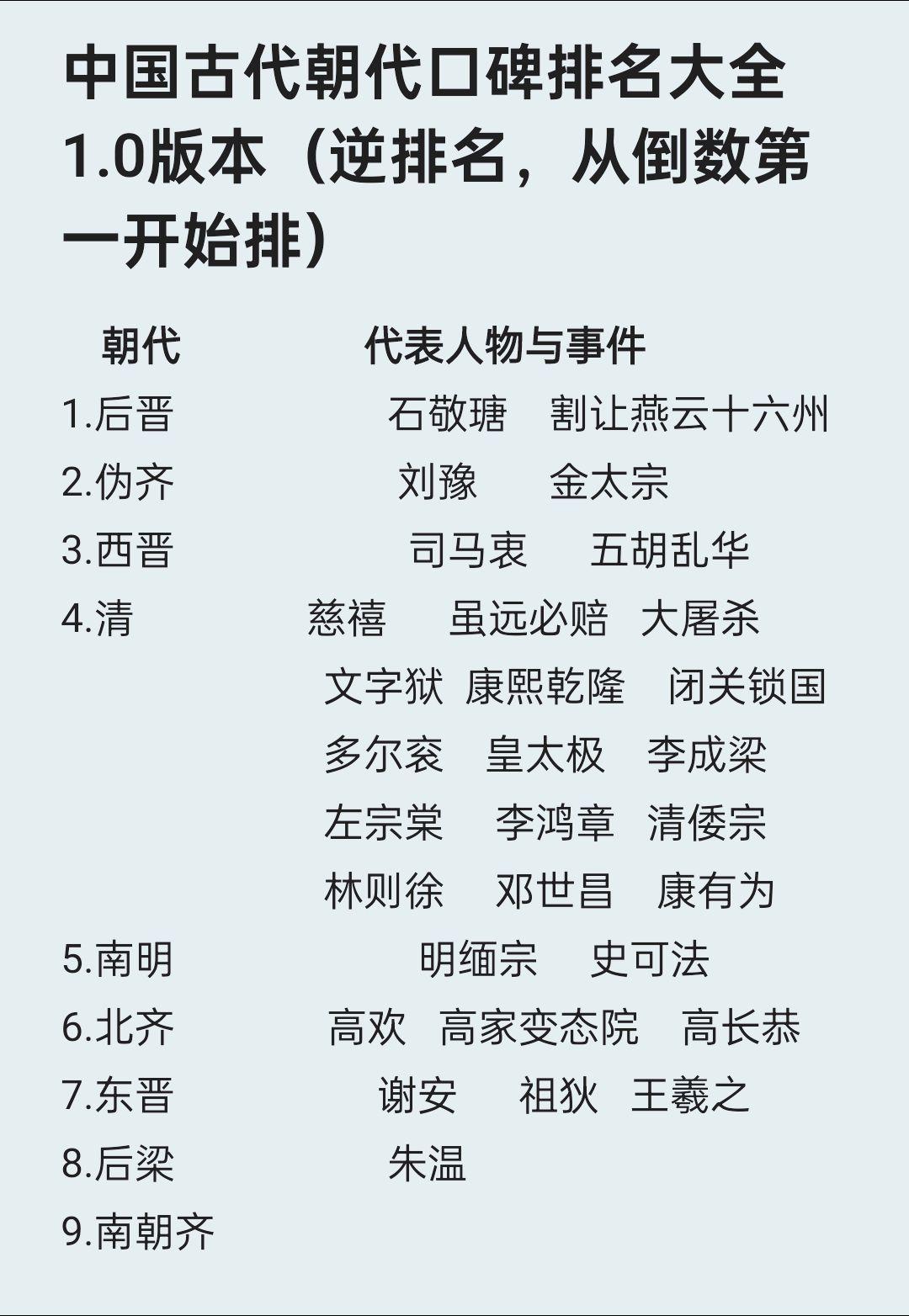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湘军大佬曾国藩患上了失眠症。他常常“四更成眠,五更复醒”,每次想到洋人纵横中原,却无以御之,便心生忧悸。
当时,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沿岸与太平天国作战。和湖南老乡胡林翼一样,曾国藩亲眼目睹了“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天”的画面,深知中国落后的武器难以抵抗洋枪洋炮。为此,曾国藩多次购置西洋船炮,提升湘军的战斗力。
但是,洋商囤积居奇的野蛮行为,让曾国藩更加emo。洋商知道湘军造不了枪炮,一颗普通的12磅炮弹就要卖他们30两银子,还有一次,曾国藩命人购置一艘轮船,说好了要装5000斤火药运过来,可洋人只顾着装自己的茶叶,根本不肯装火药,还把曾国藩派来购船的人赶下船来。
面对洋人挟技自重的蛮横态度,曾国藩下定决心,“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1861年9月11日,安庆战事结束仅过6天,曾国藩就将他的大本营移至这座军事重镇。他一边将目光投向太平军的老巢天京(今江苏南京),一边着手开始他的洋务事业。

▲曾国藩(1811-1872)。图源:网络

曾国藩进驻安庆后,一批对西学深有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集结到他的麾下。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曾国藩邀请“通几何算学”的华蘅芳与“修理器具技艺精巧闻名”的徐寿来到安庆,当他的“技术幕僚”。不久后,曾国藩上书保奏,请朝廷赐予他们官衔,以此拉拢更多知识分子。
精通数学的浙江海宁人李善兰(1811-1882),听说曾国藩在招募人才,也带着满腔抱负前往安庆。
作为西洋学冲击下的近代知识分子,李善兰的人生经历极具代表性。
李善兰自小就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从翻阅其父亲书架上的汉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到自学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于算学用心极深”,擅长各类函数。后来,他用“垛积术”推出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数学公式。
然而,在数学领域颇有造诣的李善兰始终放不下一件事,那就是,科举考试。李善兰一生多次应考,但屡战屡败,年过半百了也没混上一官半职。李善兰迫于生计,只能跟王韬等人一同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开始了和洋人合作翻译西方著作的职业生涯。
每次和好友王韬喝酒聊天,李善兰都要宣泄浪迹洋场的无奈之情,期盼着有一日求取功名,踏入士大夫的行列。当时,江苏巡抚徐有壬也是个数学达人,跟李善兰颇有交情。李善兰就对王韬说:“今君青先生(徐有壬)在此,予绝不干求,待其任满时,请其为予攒资报捐,得一州县官亦足矣。”后来,太平军攻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李善兰的心愿也就无法达成。
像李善兰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他虽致力于西学,在数学界著述颇丰,却仍以科举为正途,想要抱上达官显宦的大腿。为此,李善兰辗转来到了曾国藩的幕府。
求贤若渴的曾国藩对李善兰礼敬有加,于是,李善兰又向曾国藩推荐了熟谙洋务的张斯桂、张文虎等人。张斯桂到湘军后,也得到重用,奉命督造火药、训练洋枪炮队,接着,他和李善兰又举荐了他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朋友——中国留学生之父、广东香山人容闳(1828-1912)。
容闳是第一个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但回国后不受清廷重视,只能在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太平军横行江南时,容闳一度把上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有过联系。当老友们写信邀请容闳到安庆与曾国藩会面时,容闳还以为是曾国藩得知他与太平军的关系,想要摆下鸿门宴,把他骗去杀掉。
容闳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安庆,却看到曾国藩礼贤下士,诚恳地请他襄赞洋务,帮忙出国采购机器。容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虽然他的丝茶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那毕竟不是他的志向所在,只有为曾国藩效力,才能真正地一展才学。因此,容闳自豪地说:“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

▲容闳(1828-1912)。图源:网络
此时,太平天国已近强弩之末,曾国藩的湘军高歌猛进。
在曾国藩驻扎安庆的4年间,一帮人才汇聚于此,志趣相投的他们时常一同研究西学,讨论洋务。时人回忆说:“此数人者,每相往来,屡次集会,所察得格致新事新理,共相倾谈,有不明者彼此印证。”
在蒙昧初开的年代,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不讨论孔孟之道,却大谈洋务运动,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场景。

广州人冯焌光(1830-1878),是这一时期来到安庆的西学人才之一,通晓地理、算学、制船制炮之法。有一次,他负责从广州购置一批“千里镜”运到安庆。
所谓“千里镜”,即望远镜,在战场上是刺探敌情的绝佳工具。曾国藩对这玩意儿充满好奇,他先称赞冯焌光“处置甚妥”,然后亲自验货,拿起一对“千里镜”到楼上眺望。
是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千里镜,在楼上试验,果为精绝,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曾国藩从千里镜中看到的,不止是远处的景物,更是清朝与西方的现实差距。他对西洋科技充满了惊奇,又心生羡慕,更有甚者,是感到恐惧。曾国藩知道,研制新式武器,已经刻不容缓。
曾国藩网罗一大批西学人才,正是为了“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筹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晚清时期的安庆,是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发源地。图源:网络
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在战乱中应运而生。之所以称为“内军械所”,是指该厂产品主要提供湘军内部使用,同时,运营资金、技术人员等也来自湘军内部。作为近代中国新式工业的嚆矢,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其中有建造轮船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以及仿造西式枪炮的冯焌光、龚之棠、丁道杰等。
安庆内军械所成立一年后,徐寿、华蘅芳等人成功造出第一台中国人自主制造的蒸汽机,因为这台蒸汽机主要是为了解决轮船的动力问题,故曾国藩在其日记中写作“火轮船之机”。
徐寿和华蘅芳都是江苏无锡人,也是较早为曾国藩擢用的近代科学家。徐寿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人,而且率先为国人翻译了化学元素名;华蘅芳擅长数学,著有《行素轩算稿》。在造蒸汽机的过程中,华蘅芳负责测算数据、绘制图纸,徐寿负责研制机器,他们是用较为原始的手工方法,将蒸汽机需要的零件一一制造出来。
安庆内军械所的第一台蒸汽机发出响声后,曾国藩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火轮机”图。图源:网络
之后,徐寿、华蘅芳继续研制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他们先是试造了一艘木壳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但它的时速只有13里。
经过两次尝试,徐、华二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于是改暗轮为明轮,改低压蒸汽机为高压蒸汽机,提升了轮船的速度。新的轮船下水试航后,顺流时速为28里左右,逆流时速为16里左右,比初次试验时有所进步。曾国藩为其命名为“黄鹄”号。这艘轮船的全部器材,包括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由徐寿及其子徐建寅亲自监制,共耗费8000两白银,可载重25吨。《字林西报》称,这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
安庆内军械所不靠洋人的协助,仅靠一批西学人才就试制了轮船、西式枪炮,在生产上以手工仿制为主。它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造出的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而仿制的西式枪炮在投入使用后也频频发生事故。可以说,安庆内军械所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中成效不大,但的确有首创之功。
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后,内军械所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军械所”,后来因为缺乏新进展,于1866年并入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

▲1873年,金陵机器局仿制比利时的蒙蒂尼机枪。图源:网络

同治元年(1862),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上海期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他创立的淮军抵沪,抵挡太平军。之后的两年内,李鸿章在上海相继设立了三个洋炮局,仿造西式枪炮,用于装备淮军,并聘请英、法教官训练淮军。据统计,这三个洋炮局,在两年间花费了淮军军饷拨用经费28.8万余两。
其中,位于上海松江城外的洋炮局,因聘请英国人马格里主持该局事务,又称“马格里洋炮局”。马格里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本来是参与对抗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成员,后来辞去常胜军职务,加入淮军,跟随李鸿章十多年,帮李鸿章督造炮弹、主持新式兵工厂,为了表示对清朝的亲近,还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清臣。这所洋炮局先后迁至苏州、南京,即金陵机器局的前身。
在上海筹办洋炮局期间,李鸿章发现,当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设备落后、生产技术低下、产品质量较差,尚未能学到西洋兵器的精髓。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写了封信,寄给在北京主持洋务大局的恭亲王奕訢,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一篇极具价值的文章。李鸿章在文章中号召士大夫改变传统观念,正视西洋科技的先进性,他还希望朝廷能率先推行变革,为“制器之人”专设一科取士,使更多知识分子转向西学,并获得富贵功名。
更难得的是,李鸿章在这篇《致总理衙门函》里不只提到了英、法等国的船坚炮利,还说到,日本区区海外小国,已经“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假以时日,恐怕他们会成为一个心腹大患。
在此背景下,1865年,李鸿章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派苏松太道道台丁日昌买下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了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另外两个洋炮局,并接收了曾国藩派容闳赴美采购的机器,随后于上海创办了比此前的兵工厂设备更精、规模更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
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筹办的军工企业,其领导一般由通商大臣或总督任命,为首的叫“总办”,副职称“会办”。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任总办是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1823-1882),他曾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弹,后来到上海协助李鸿章筹办洋炮局,也是个老“洋务派”了,两名会办分别由沈保靖和冯焌光担任,前者长期为淮军采办军火,后者是曾国藩在安庆提拔的人才。此外,江南制造总局有别于安庆内军械所的一点是,技术工作由洋人负责(称为监工)。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图源:网络
江南制造总局创建的第一年,用于生产设备的经费就有25万两左右,这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
如此庞大的开支,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到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每天可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炮弹100发。1868年,第一艘中国制造的600吨位铁壳明轮船成功下水,驶至南京。尚未调任直隶的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为这艘船取名“恬吉”,取“四海波恬, 厂务安吉”之意,这艘轮船的速度和载重,都比安庆内军械所造的轮船有所突破,可装炮8尊。
在江南制造总局创建后的10年间,这座兵工厂已经可以制造来福枪、林明敦枪等西洋军械,制成了与“恬吉”号相仿的兵轮2艘,取名“操江”、“测海”,并在之后更进一步,制造排水量、马力、装炮数量更高的“威靖”、“海安”、“驭远”等船舰。
到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累计生产了5.2万支洋枪、408万磅火药、588尊炮和8艘兵船,另有枪弹、炮弹、鱼雷、铜引等不计其数。
但江南制造总局存在的劣势也很明显,它所能造的兵器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兵器比较,仍有10年以上的差距。另外,江南制造总局的运营成本极高,到1894年,其累计经营总计达875万两,这其中一大部分要用于进口材料。有学者分析,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船至少要贵一倍。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林明敦式后膛来复枪,造价高于进口,质量也不如进口武器。这就陷入了“造不如买”的尴尬处境。

曾国藩和李鸿章交出各自的答卷后,左宗棠也开始行动了。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
顾名思义,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标是造船。这笔费用比制枪造炮更加巨大,因此,左宗棠筹办船政局之初,便提出了5年内需要300万两的经费预算,并且提出了短期内制造16艘轮船以及训练一批工匠、船员的规划。
为此,左宗棠找来了两个帮手——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
日意格和德克碑的来历跟前文提到的马格里比较相似,他们本是中法混合军“常捷军”的军官,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跟左宗棠有不错的私交。常捷军解散后,他们由法国领事连署,签订“保约",加入福州船政局,担任监督。
得知左宗棠争取到法国支持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十分不满,认为此举将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于是从中挑拨,想将法国人踢出去。但日意格等人据理力争,甚至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阐明与清廷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才使法国政府没有放弃对中国办船厂的支持。此时,中法两国还想不到,十多年后,双方会在这里爆发一场海战,并让辛苦建立的福建水师几近覆没。

▲日意格(1835-1886)为福州船政局付出多年心血,中法战争期间,他不领薪水,继续留华照料船政学员。图源:网络
不过,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其实有极强的主权意识。他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
左宗棠认为,造船可以满足军用和民用两个用途,不仅可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避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洋人轮船直达天津的局面再度出现,还可以发展运输业和商贸业,增强与外商的竞争能力,商用的收入也可以反哺为船厂的经费(“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
左宗棠创立福州船政局后不久,就被调任陕甘总督,接替他的是原本丁忧在籍的江西巡抚沈葆桢。
作为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就任福建船政大臣后,积极投身于船厂事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福州船政局的工厂、仓库陆续建成。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这艘船排水量1450吨,马力150匹,可装炮6尊。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能在没有欧洲人员的帮助下制造轮船,并培养了数百名工匠,于是遣散了之前聘用的洋匠。截至这一年,福州船政局共计制造各式轮船15艘,基本完成了左宗棠的计划。
在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的推动下,洋务运动的军工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到1894年,先后出现了34个官办军工企业,遍及18个省,其中较为知名的还有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

▲湖北枪炮厂。图源:网络

为了培养适应洋务运动的新式人才,清政府设立了一些文化教育机构,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等。
京师同文馆起初只是一座“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后来转向多学科教学。为此,恭亲王奕訢上奏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
奕訢认为,要自己制造枪炮,一定需要懂科学的人才,所以要请外国人来教朝中的青年官吏。于是,同文馆专门划定了招生范围: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年龄在30岁以下者,可经考试录取后入馆学习。
朝中顽固派(保守派)得知同文馆要添设科学班,请外国人当老师,还要招收翰林院的士子做学生,认为此举是对祖宗之法的亵渎,甚至可能动摇国本,纷纷进行抨击。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理学家倭仁和恭亲王奕訢的论战就发生于此时。
因此,最初参加同文馆考试者仅有72人,考试后录取30名,翌年因学习不合格者再淘汰20名,洋务派在朝中遭受的抵制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因为倭仁在反对此事的奏折中说,不必请外国人当老师,中国也有很多科技人才,朝廷特意让倭仁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倭仁这下囧大了,干脆称病不干。不过,后来洋务派还真的找了一位教算学的中国教习,他就是被调进京的李善兰。
李善兰一生都想求取功名,到同文馆后总算被“钦赐中书科中书”,从七品,他晚年在京,“名公钜卿,皆折节与之交,声誉益噪”,直到1882年去世前几个月,勤学不辍的李善兰还在撰写《级数勾股》二卷,堪称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先驱。
1869 年,美国人丁韪良继任总教习后,京师同文馆相继开设了汉文算学、洋文天文、洋文算学、格物测算、公法学、汉文化学和医学等课程。

▲李善兰(1811-1882)。图源:网络
顽固派的反扑依然凶猛。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书,声称制造船舰靡费多而成船少,应该让上海、福建两局暂停制造。宋晋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祀典、礼仪之类的工作,对实干知之甚少。
因此,李鸿章对宋晋的观点予以驳斥。他说,国家各项费用都可节省,唯有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的费用“万不可省”,不然,“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对此,李鸿章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船,节省下的费用用来造新式船;二是让上海、福建二局兼造商船,供华商使用,让华商自立公司,与洋商竞争。
李鸿章的主张是:“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这便是洋务派除了自强之外的另一个口号——求富,洋务派此后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即这一主张的体现。
另一方面,各派势力的交锋,也预示着朝中的暗流涌动。
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对奕訢筹办洋务一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慈禧太后可能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二者的矛盾最终导致中法战争之后的“甲申易枢”,1884年,奕訢受弹劾后被迫下台,居家养疾,慈禧任命自己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改组军机处。

▲19世纪70年代的总理衙门。图源:网络
在地方,洋务派兴建的兵工厂内部,也存在腐化、僵化的情况。
在江南制造总局任职的英国翻译家傅兰雅发现,他为洋务运动翻译的书,只有制造局内几个部门可以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极少,无法在社会上取得广泛的影响。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间,发现有一些职员是达官贵人的亲戚,难以管理,而且船政局的采办系统经常出现侵吞公款的现象,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质量堪忧。
在晚清的改良运动中,类似的新旧冲突屡见不鲜。
历史学者秦晖在《传统十论》中讲“西儒会融”的现代化之路,有一段论述:
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 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洋务派任重而道远,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参考文献: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中华书局,2018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
[清]王韬:《王韬日记》,中华书局,2015
[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19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秦晖:《传统十论 :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