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锦戏是明朝宫廷戏剧的一种,在明朝之前的文献中未见记载,清代及以后的文献亦未载录其演出实况。清人高士奇称过锦“迨入我朝遂废不治”[1],程恩泽诗云:“水嬉过锦未亲见,剩有轻罗拜恩久”,[2]翁心存诗曰:“过锦排当想像中,胜朝曾此建离宫”[3],这些均表明过锦戏是明朝特有的名称,后人对过锦戏的认识唯有凭悬想而已。

《明代宫廷戏曲编年史》
就演出形式、表演形态而言,过锦戏继承了宋金杂剧滑稽逗乐的传统,并稍加改变,规模上略有扩大。它以其命名之新奇引起了戏曲研究者的兴趣,学者对其加以考察的主要依据是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
从清人提及过锦戏的文献来看,乾隆时期之后的学人对它已非常陌生,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曲解,误导了后人。胡忌的《宋金杂剧考》是对过锦戏的演出形态、体制等做较早、较深入研究的成果,其他学者的相关探讨亦对理解过锦戏有所助益。
然而,笔者仔细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过锦戏研究有三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辨正:一是清代以来关于过锦戏的种属所存在的一些误解;二是关于过锦戏的形态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是关于过锦戏的演出规模的不同见解。这些均需基于相关文献载录一一予以分析辨正。
以下即针对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力争对过锦戏研究有所推进。

根据明代宫词等史料文献的记载,过锦戏在明朝宫廷内经常上演,娱乐性非常突出,十分受欢迎。秦徵兰诗曰:“过锦阑珊日影移,蛾眉递进紫金卮。天堆六店高呼唱,瘸子当场谢票儿”[4]。饶智元诗云:“水嬉过锦绝欢娱,内殿宣传罪己书。忧及万方多涕泪,比来长御省愆居”[5]。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吴伟业、屈大均等亦曾吟咏及此。
清代再也没有宫廷演出过锦戏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人对它的认识日趋模糊。很多人仅仅知道它是明朝宫廷戏的一种,至于具体面貌则不得而知了。例如,晚清俞樾在阅读吴伟业《琵琶行》中“先皇驾幸玉熙宫,凤纸佥名唤乐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玲珑”等诗句时,对过锦究竟属于何种戏曲已不甚明了。当后来看到刘若愚《酌中志》对过锦戏的记载,才对此有了一定了解[6]。

《清代宫廷承应戏及其形态研究》
以俞樾之博闻强识尚且如此,其他人产生误解亦不足为奇。整体来看,清人对过锦戏主要存在两种误解,并均对后来学界相关研究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下面分别予以梳理、辨明。
一种意见认为过锦戏是影戏,以清朝乾隆时期的吴长元为代表,他说:“明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內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按:过锦,今之影戏也。”[7]
按语之前的文献引述并无问题,但是吴长元所加按语“过锦,今之影戏也”并无根据,不免有臆测之嫌。揆其致误之由,盖因未能细读所引文献的上下文所致。
吴氏引文源自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增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明史职官志》。”
于敏中在此注明其文献源于《明史职官志》,其中并无过锦戏即影戏之说明,不知吴长元何所据而云然。《日下旧闻考》此条记录之前是:

《日下旧闻考》
原钟鼓司陈御前杂戏,削木为傀儡,高二尺余,肖蛮王军士男女之像,有臀无足,下安卯栒,用竹板承之,注水方木池,以锡为箱,支以木凳,用纱围其下,取鱼虾萍藻践(笔者按: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践”当为“跃”之误。)浮水面,中官隐纱围中,将人物用竹片托浮水上,谓之水嬉。其以杂剧故事及痴儿騃女市井驵侩之状,约有百回,每四(笔者按: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当为“回”之误。)十余人,各以两旗引之登场,谓之过锦。皆钟鼓司承应。《芜史》。[8]
于敏中根据刘若愚《芜史》记载了水嬉和过锦两种宫廷杂戏,其中水嬉是以木材削制成傀儡人物,由太监隐藏于纱围之后,“将人物用竹片托浮水上”来表演的。
而过锦则是“以杂剧故事及痴儿騃女、市井驵侩之状,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各以两旗引之登场”加以表演的,两者虽然均属“钟鼓司承应”,却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两者皆与影戏无关。
影戏是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据宋代《都城纪胜》“影戏”条记载:“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9]
影戏表演是艺人通过操纵纸影、皮影或手影形成的形象来完成的,而过锦戏则是演员真人登场扮演故事,两者依托的物质媒介和表演形式完全不同。由是观之,影戏不是过锦戏。虽然水嬉和影戏均是通过人的操控进行表演,但是从制作材质和表演形式来看,水嬉是水傀儡,属于傀儡戏之一种,必须在水上表演,与影戏也无直接关系。
清人铁保《玉熙宫词》:“嘈嘈杂剧名过锦,绰约轻旂对对引。雅俗全登傀儡场,君王何处窥民隐。水嬉之制制更神,雕刻木偶投水滨。机缄运制百灵走,出没邋遢如生人。”[10]

《清铁保书自序诗稿册》
前四句咏的是过锦戏,后四句写的是水嬉。“嘈嘈杂剧名过锦”,指过锦是杂剧的一种,表演起来非常热闹。“水嬉之制制更神,雕刻木偶投水滨”,指水嬉是在水里表演的木偶戏,即水傀儡,“机缄运制百灵走,出没邋遢如生人”是说水嬉的演出像真人表演一样栩栩如生。
今人汤际亨根据吴长元之说得出结论:“可知明朝影戏已见盛行,宫廷内且有专司之官”,此说前提有误,断语自然难以信从。
另外,至今未见明朝宫廷有专司影戏之官的记载。针对此说,江玉祥征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禁中演戏”、刘若愚《明宫史》木集“钟鼓司”、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等文献的相关记载,较为细致地考辨了过锦戏并非影戏[11]。其说甚为允当。
此外,郝可轩征引吴长元按语称“皮影戏在明朝时名‘过锦’”[12],学者型作家高阳以为“皮影称为过锦”[13],想必也是受吴长元之说的影响。
另一种意见以为过锦戏是木偶戏,以晚清的震钧为代表。他说:“明代宫中有过锦之戏。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此疑即今宫戏之滥觞。但今不用水,以人举而歌词。俗称托吼,实即托偶之讹。《宸垣识略》谓:‘过锦即影戏’。失之”[14]。

《宸垣识略》
近人夏仁虎《傀儡戏》诗:“日长无事慰慈怀,内里传呼过锦来。春耦斋中风景好,玲珑特构小宫台。”其自注云:“傀儡戏俗呼托吼,即明代之过锦。清曰宫戏,以娱太后、宫眷。其演唱技艺皆由内监供役,故亦称宫戏,于春耦斋构宫台。自孝钦后,外优入演,此戏遂废”[15]。章乃炜等《清宫述闻续编》采纳其说[16]。
震钧、夏仁虎均认为过锦即托吼,后者进一步坐实过锦为清代宫戏,考虑到夏仁虎稍晚于震钧,受震钧影响的可能性大一点。
托偶是木偶戏的一种,张次溪云:“托偶戏之偶字,北京读偶如吼。此种戏约分三种,一种名傀儡,一名提线,一即此种,名曰托吼”。
托偶的表演与形制是“以其真人皆须隐藏帐内,不得窥视外边,而观者亦只见偶人,不见真人,极便于宫中观看,故又名大台宫戏。其舞法则上搭一戏楼,下截四周,围以布帐,人在帐中,托偶人舞之,故名托偶。每一真人,舞一偶人,一切喜怒哀乐,皆可形容出来。”[17]
也就是说,木偶戏是藏在幕后的每个真人通过操控一个偶人来表演的,观众是完全看不见操纵者的,而过锦则是演员真人登场扮演,插科打诨,观众欣赏的是真人的表演。两者依托的物质媒介和表演形式不同,显系不同的表演伎艺。由此可知,震钧指出吴长元之失是歪打正着,其“过锦即托偶”之说也是错误的。
根据前文所引《琵琶行》《日下旧闻考》《玉熙宫词》的片段可知,震钧显然是混淆了过锦与水嬉两种杂戏。

《明宫史》
明人刘若愚详细记录了水嬉的制作与表演体制:
又,水傀儡戏,其制用轻木雕成海外四夷蛮王及仙圣、将军、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余,止有臀以上,无腿足,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长三寸许竹板承之,用长丈余、阔数尺、进深二尺余方木池一个,锡镶不漏,添水七分满,下用凳支起,又用纱围屏隔之,经手动机之人,皆在围屏之内,自屏下游移动转。水内用活鱼、虾、蟹、螺、蛙、鳅、鳝、萍、藻之类浮水上。圣驾升殿,座向南。则钟鼓司官在围屏之内,将节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钟鼓喧哄。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采。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惟暑天白昼作之,犹耍把戏耳[18]。
由上引文献可知,水嬉(即水傀儡戏)表演的题材比较丰富,其中军事战争题材有英国公三败黎王、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等故事,神怪题材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等故事,表演之时“钟鼓喧哄”,非常热闹。
其表演形式才是震钧所谓“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采”即震钧所谓“旁人代为歌词”。水嬉是通过人操控木偶浮在水上表演,而托偶是通过人托举木偶表演,它们之间的区别才是“但今不用水,以人举而歌词”,显而易见,过锦并非托偶。

《明代宫廷戏剧史》
震钧此说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李家瑞征引震钧之说以证明悬丝傀儡与水傀儡在明代都没有消失的观点,[19]佟晶心在论证傀儡戏时亦引证震钧之说[20]。孙作云称:“按过锦之戏,其说非一,果如《天咫偶闻》所说,‘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当即水傀儡无疑。”[21]
他十分清楚关于过锦戏“其说非一”,却在诸种说法中误信了震钧的意见。雷齐明也根据《天咫偶闻》认为过锦戏与木偶戏有类似之处[22]。
其他文史研究者亦多受震钧误导,如王娟以为:“水傀儡:古称水饰、水戏、水嬉……后来进入宫廷,被称为宫戏与过锦戏”[23]。周耀明说:“水傀儡戏又叫‘过锦戏’”[24]。吴刚、冯尔康等也或多或少受到此说的影响[2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者中还有将过锦、水嬉混淆的,有的以为有所谓“过锦水嬉”之戏,有的认为有所谓“水嬉过锦”之戏。前者如傅起凤等认为:“过锦戏除上述形式外,有时也在水中表演。
据《续文献通考》载,愍帝朱由检(1628—1643在位)曾宴玉熙宫,作过锦水嬉之戏。曹静照宫词云:‘口敕传宣幸玉熙,乐工先侯九龙池;妆成傀儡新番戏,尽日开帘看水嬉’。文献还记载,朱由检曾数次观看这种过锦戏”[26]。
然而,《续文献通考》注明是根据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作如上记载的,并未将两者混淆,而《金鳌退食笔记》对过锦、水嬉是分别介绍的,两者界限分明[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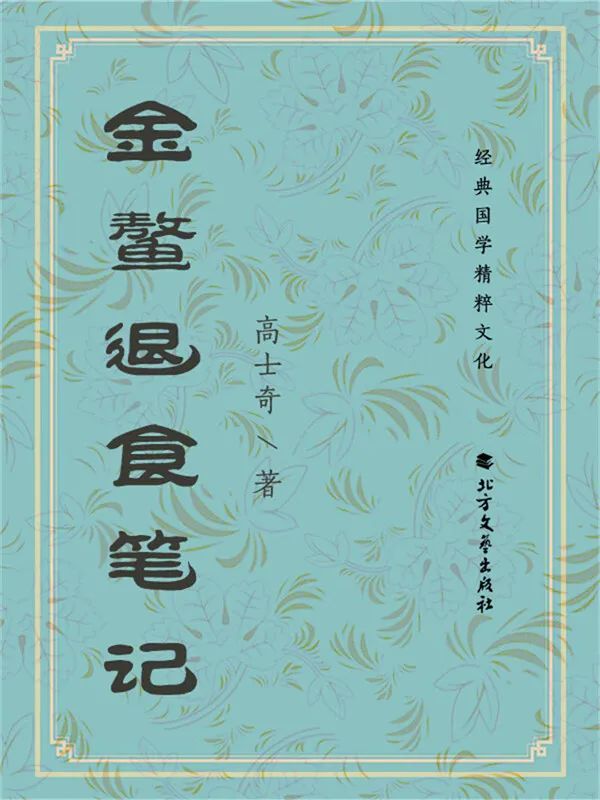
《金鳌退食笔记》
另外,曹静照宫词只描述了水嬉的表演,并未提到过锦。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的简释者云:“《金鳌退食笔记》载,崇祯帝每宴玉熙宫,作‘过锦水嬉’之戏。”[28]
后者如荆清珍认为过锦之戏又叫水嬉过锦[29],其依据是:“《芜史》御前杂戏有水嬉过锦,皆钟鼔司承应”[30]。
此引文前的条目虽为“水嬉过锦”,但姚之骃显然明白水嬉、过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否则就不会说“皆钟鼔司承应”。“皆”,俱词也,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止一个。如果姚之骃认为水嬉过锦是一种艺术形式,绝不会用“皆”字。
高志忠认为:“过锦戏中有一种叫做‘水嬉过锦’的值得一提。《柳亭诗话》卷18 ‘过锦’条云:“何次张宫词‘昆明池水漾春流,夹岸宫花绕御舟,歌舞三千呈过锦,琵琶一曲唱梁州。’盖在水上进行演出的过锦之戏为‘水嬉过锦’”[31]。

《明代宫廷戏曲与外交研究》
然详考其所引文献,仅提及过锦而未涉水嬉。所谓“歌舞三千呈过锦”当指在众多歌舞表演中穿插了过锦戏的表演。“盖在水上进行演出的过锦之戏为‘水嬉过锦’”之说不知何据?以上诸位之所以产生误读,可能是因为水嬉、过锦在文献中经常被同时提及,将两者连读而未参考其它相关文献所致。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过锦戏的形态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过锦戏与杂扮相似,以王国维为代表。作为近代最早关注过锦戏的学者,他指出:“则元时戏剧,亦与百戏合演矣。明代亦然。吕毖《明宫史》(木集)谓:‘钟鼓司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说笑话之类,又如杂剧故事之类,各有引旗一对,锣鼓送上。所装扮者,备极世间骗局俗态,并闺阃拙妇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杂耍把戏等项。’则与宋之杂扮略同。”[32]
这一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如周贻白据《酌中志》记载认为:“‘过锦戏’虽有戏剧的形式,而无戏剧的排场,仅为活动地随上随下。颇与宋代所谓‘杂扮’相仿,或即由其转变而别立新名,亦未可知”[33]。
董每戡以为:“照沈氏所说,明代的‘过锦戏’只名称新鲜,实际内容跟笑乐院本是差不多的,仍然是唐代参军戏,两宋杂剧,金元院本的继承,甚至没有什么发展和提高,只不过取了这么个漂亮名儿罢了……可是依书本上的一些零星记载看来,它大致是放在正戏完后‘打散’用,有点儿象两宋杂剧的最后一段‘杂扮’”[34]。
赵景深等认为,过锦戏是宋杂剧中杂扮的延续[35]。上述诸家注意到过锦与杂扮的相似处,但用“略同”“相仿”“有点儿象”等词语表述,未遽下断语,态度严谨。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赵景深文存》
过锦戏与杂扮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和谐谑性,结构都比较简短,场面皆十分热闹。然而它们又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量齐观,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表演的次序(位置)不同。杂扮在正杂剧的结尾表演,也称打散。据《梦粱录》记载:“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36]
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品题》云:“盖扮杂剧至末折尾声止,正剧虽完,而当场之艺犹未结束,观者犹未去也。至打散讫而承应之事始毕。打散乃正剧之后散段,其事实为送正剧而作者”[37]。过锦戏则不然,其表演位置较为灵活,不拘于正戏之末,既可以在正戏之前搬演,又可以在正戏之中进行,亦可以在正戏之后演出(说详后)。
二、表现的题材不同。杂扮装扮的人物是乡村老叟,地域范围局限于山东、河北,题材是嘲谑这类人物的孤陋寡闻,即所谓“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
而过锦装扮的人物则是市井人物,地域范围没有限制,题材也相对广泛,包括“世间骗局俗态,并闺阃拙妇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等内容,并不专以戏弄庄稼人为能事。因此,尽管过锦戏与杂扮很相似,但不能等同。

《昆剧演出史稿》
第二种观点以为过锦戏包括说笑话、滑稽戏和北杂剧及杂耍把戏三种形式,以陆萼庭为代表。
他说:“‘过锦’何解?自来众说纷纭,或谓即‘今之影戏’,或谓系宋杂剧之别立新名。细味引文表述层次,所谓过锦其实含有‘多样’的意思,并非单一的戏剧形式名称。其事甚古,刘若愚虽经目睹,惜不明渊源,以致分厘不清,叙述失序。‘每回’指每档节目,‘百回’极言其多而已。这里至少包含三种形式:一说笑话、滑稽戏,渐伴有乐声歌呼动作以渲染气氛,应该与‘御前插科打诨’是一物,是宋元杂剧原本的遗制,有传统段子,更多是新编的;二北杂剧,新旧兼有;三杂耍把戏,所演节目今知有狻猊舞(狮子舞)、掷索、垒七桌、齿跳板、蹬技等。我认为明代的宫戏实际囊括了宋代的‘杂伎艺’,名副其实的沿‘金元之旧’”[38]。
陆先生敏锐地指出过锦戏并非单一的戏剧形式名称,具有多样的意思即杂的特征,过锦戏确实包括不止一种体制。
但是以为北杂剧也是过锦戏之一种则值得商榷。根据前引《酌中志》《明宫史》对过锦戏的记载,过锦戏的题材以“世间骗局俗态,并闺阃拙妇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为主,而北杂剧的题材包罗万象,十分广泛,明显不同于过锦戏。
过锦戏的艺术特征是“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即以诙谐热闹的插科打诨收场,而北杂剧则或悲、或喜、或悲喜交乘,插科打诨只是其中的调料而已,并不构成戏剧的主体,绝大多数也并非作为杂剧结局之用。考引文所载 “杂剧”故事当指沿金元之旧的院本,与以正旦、正末为主角演唱四大套曲的偏重叙事的北杂剧是不同的。因此,北杂剧不属于过锦戏的范畴。
第三种观点认为过锦戏就是院本,以胡忌为代表。

《宋金杂剧考》(订补本)
他认为:“在他处未见‘过锦’资料前,据前引四例,我们不妨说:明代宫中所演出的院本尚有‘过锦’的别称。而且就这些记载看来,过锦应属于优谏类的滑稽戏而不是歌舞类戏。自南戏、北曲杂剧相继盛行以来,院本即相对属于小戏之流,以《金瓶梅词话》和《客座赘语》证之,它仍然有夹杂在杂耍、队舞、伎艺之间演出的。‘过锦’的‘过’,似有夹带的含义;‘锦’字可能约如现今习惯语‘什锦糖’‘十样锦’之类(南曲集曲中有‘五样锦’也正同此义),有零碎、好玩的意义”[39]。
说过锦是院本的别称,显然以为过锦戏就是院本。廖奔也认为:“很明显,过锦戏就是院本,其表演要求‘浓淡相间’,不是令人想起唐代参军戏的‘咸淡最妙’”[40]。
此说有一定道理,似尚可补充一则资料以证之。《明史》记载:“阿丑,宪宗时小中官也,善诙谐。帝尝宫中内宴,钟鼓司以院本承应,为过锦戏,丑毎杂诸伶中作俳语,间入时事,帝辄喜,或时作问之以为娱,而丑顾心疾汪直弗置也”[41]。
揆“钟鼓司以院本承应,为过锦戏”之意,则院本显然属于过锦戏的表演形式之一。
明人沈德符云:“有所谓过锦之戏,闻之中官,必须浓淡相间、雅俗并呈,全在结局有趣,如人说笑话,只要末语令人解颐,盖即教坊所称耍乐院本意也。”[42]此处明确交代其关于过锦的信息是“闻之中官(宦官)”,说明沈德符并未亲眼看过过锦戏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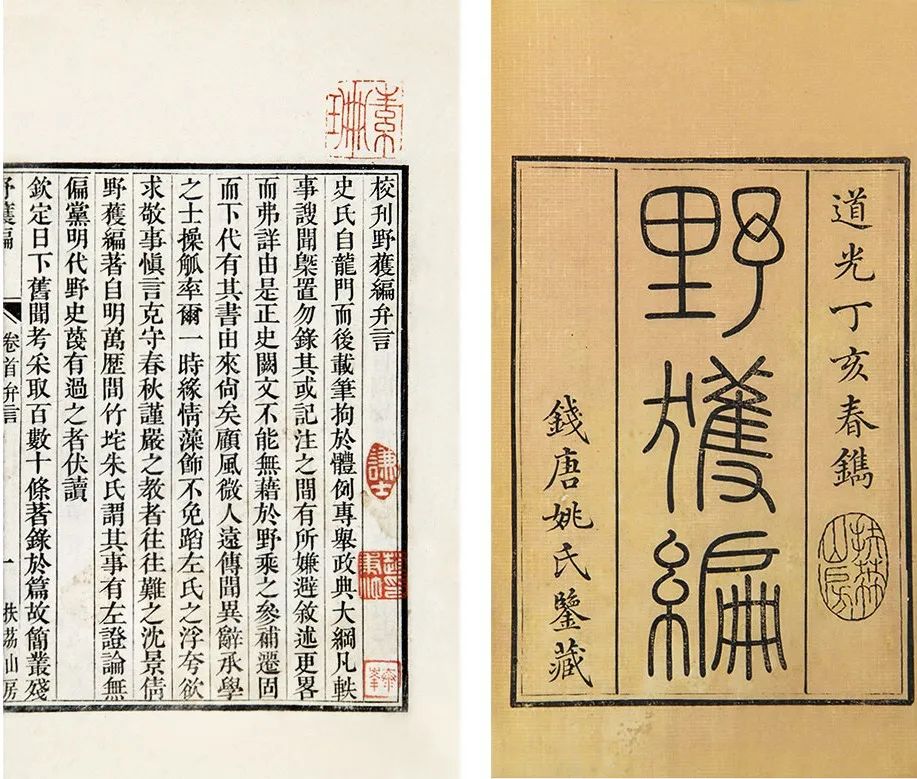
《万历野获编》
鉴于他与刘若愚年代相近,生活或有交集,其所谓“闻之中官”的“中官”很可能即指刘若愚。即便并非如此,也不妨碍亲眼看了过锦戏表演的刘若愚所记更加可信,其《酌中志》记载过锦戏时明确指出:“杂耍把戏等项,皆可承应。”[43]意即杂耍、把戏亦是过锦戏的表演内容。
杂耍把戏是杂耍与把戏的合称,两者往往有交叉。明人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称:“杂耍则队舞、细舞、筒子、筋斗、蹬罈、蹬梯”[44]。清人李斗记载,杂耍之技包括竿戏、饮剑、壁上取火、席上反灯、走索、弄刀、舞盘、风车、簸米、躧高跷、撮戏法、飞水、摘豆、大变金钱、仙人吹笙等[45]。除了撮戏法、飞水、摘豆、大变金钱属于魔术,其余均属于杂技。把戏亦兼指杂技和魔术。
明传奇《蕉帕记》第三出“下湖”形象地描述了把戏表演:“﹝中净﹞列位相公在上,看小的做一会把戏讨赏。﹝净﹞妙妙!你有什么本事?﹝中净带做介﹞﹝北寄生草﹞﹝中净﹞卖解单身控。﹝生﹞会走马的了。﹝中净﹞千钧只手拿。﹝小生﹞是有手力的了。﹝中净﹞吞刀任把青锋插。﹝净﹞妙!怕人。﹝中净﹞抛丸尽着流星打。﹝净﹞看脑袋。﹝中净﹞飞枪直向云端下。﹝净﹞罢了,坏了眼。﹝中净﹞有时百尺上竿头,撒身惯使飞鹰怕。﹝净﹞掉下来跌折了腰,妙妙!好手段!”[46]此处把戏指杂技。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六所记幻戏既有魔术亦有杂技[47]。
李渔曰:“如做把戏者,暗藏一物於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际众人射覆之时也”[48]。这里把戏指魔术。章炳麟《新方言·释言第二》云:“其谓幻戏曰把戏,或曰花把戏,把即葩字,花即蒍字”[49]。则幻戏又名把戏,幻戏和杂耍有交叉重合之处,故可统称为杂耍把戏。
由此可见,过锦戏不是单一的品种,而是混杂的形态,它不仅包括以滑稽调笑为目的的院本,而且还包含非常精彩耸人视听的魔术、杂技等表演,娱乐性突出,称之“绝欢娱”名副其实,属于典型的“杂”戏。

《戏曲剧种演进史考述》

学术界对过锦戏的演出规模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以为过锦戏属于大戏之范畴,演出规模较大;另一种意见以为过锦戏属于小戏之范畴,演出规模较小。
过锦戏究竟属于大戏还是小戏,牵涉到学者对大戏、小戏的认知,而以往学者谈论大戏、小戏时,指称的往往是不同的戏曲现象,难免言人人殊。
对此,李玫、曾永义作了系统深入的辨析。李玫指出:“所谓小戏,在明清曲家对明清传奇的评论中,指传奇中某些净、丑、杂等次要角色出场的场次,或指在特定场合表演生动的配角;在清代地方戏的语境中,除了指小剧种,通常指一类表现普通人生活、且风格谐谑的短剧。这些短剧,既包括表现手法简单的民间戏,也包括那些从晚明至清代一直流传的成熟的剧作。所谓‘大戏’,除了指整本戏和连台本戏以及大剧种外,还指一类吉祥戏”[50]。

《中国民间小戏史论》
曾永义着眼于戏曲的发展史,认为:“所谓‘小戏’,就是演员少至一个或三两个,情节极为简单,艺术形式尚未脱离乡土歌舞的戏曲之总称……而其‘本事’不过是极简单的乡土琐事,用以传达乡土情怀,往往出以滑稽笑闹,保持唐代‘踏谣娘’和宋金杂剧‘杂扮’的传统。所谓‘大戏’即对‘小戏’而言,也就是演员足以充任各门脚色扮饰各种人物,情节复杂曲折足以反映社会人生,艺术形式已属综合完整的戏曲之总称”[51]。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小戏的特点是形制短小、风格谐谑、情节简单;大戏的特点是形制长大、风格多样、情节复杂。下面以此为标准考量以上两种观点。
先看第一种意见,翦伯赞在论明代戏剧时说:“在结构方面,则由‘四折剧’发展而为百回以上的长篇巨制。刘若愚《酌中志》谓:‘(明代)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由此可知明代戏剧,无论在剧曲本身音乐配合方面,都已经超越了金元时代的水准”[52]。以过锦戏证明代戏剧的长篇巨制,应是将其作大戏看待。
周妙中认为:“太监学的宫戏,有《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曲选所收的曲子,也有所谓‘过锦之戏’,以及杂耍等等的节目。只是玉熙宫档案早已散失,演出情况如何,无从作详细的了解,只可以从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得知一斑……看来所演的内容,与民间并没有太大差异,只是规模庞大得多。长达百回左右的‘过锦之戏’很可能就是乾隆年间一些宫廷历史大戏的蓝本”[53]。
王正来认为清宫大戏《劝善金科》《异平宝筏》的结构是一段一段的,乃受明代宫廷过锦的影响,可以称为清代的过锦戏[54]。李真瑜论及过锦戏时据《酌中志》所载认为:“戏长至百回,演出的内容很多,演员阵容庞大,所以场面也很宏大”[55]。

《酌中志》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均着眼于于过锦戏约有“百回”的记载,以为它既然有百回,当然是规模庞大的长篇巨制,属于大戏之属。以“回”称戏早有先例,宋人孟元老云:“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毎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56]。元人杨立斋《哨遍》套曲云:“更那碗清茶罢,听俺几回儿把戏也不村呵”[57]。元人高安道散套《哨遍·嗓淡行院》云:“打散的队子排。待将回数收”[58]。
此处回均可指可断可连的独立场次段落。据刘若愚的记载,过锦戏的形制是短小的,风格是谐谑的、情节是简单的,当属小戏,所谓百回是极言过锦桥段之多,而非像大戏那样的连贯长篇、情节复杂。
再看第二种意见,认为过锦戏类似于杂扮和认为过锦戏是院本的学者显然认同过锦戏属于小戏的观点,前文已述兹不赘引。
其他如薛宝琨以为:“明代有所谓‘过锦戏’,继承唐参军、宋滑稽遗风穿插于大戏之中,以‘浓淡相间、雅俗并陈’,‘谐谑杂发,令人解颐’取胜。敷演其中段落也绝似现代相声。”[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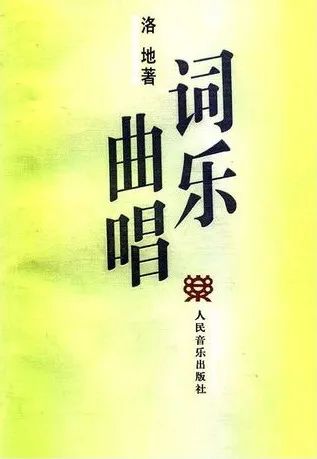
《词曲乐唱》
洛地称:“所谓过锦,大致便是若干‘锦’组练成队串连(‘过’)而演吧。包括杂耍在内的各式戏耍的‘耍乐院本’串演,称‘过锦之戏’……过锦戏(弄),将若干戏弄段子串演:以(任何)一个由头,造成或提供一个过程或背景,便可能收纳若干相近的戏弄段子,组练串连而演。其收纳的戏弄段子,相互间是平列的,段数可多可少;其中每个段子又仍保持其为段的状态,可长可短”[60]。
曾永义以为:“像这种一折或一出式的‘小戏’,明代有所谓‘过锦戏’……可见过锦戏就是‘笑乐院本’(沈氏之语),‘约有百回’,则是一个大型的小戏群,内容包罗万象,而其中既有‘世间市井俗态’及‘拙妇騃男’,则应当也包含类似‘踏谣娘’或‘纽元子’那样乡土小戏式的演出”[61]
李玫说:“从此段话看,崇祯朝,在李自成没有打到河南以前皇宫里一直演过锦戏。……这既有宋代杂剧的遗韵,又与明清的小戏作品在审美效果上异曲同工[62]。上述学者未局限于百回之说,而是从形制、风格、情节的特点出发,认为过锦戏属于小戏或小戏群,这种看法是相对准确的。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因未见学者对此分歧专门论证辨析,故立足另两则材料对此问题进一步申说。过锦戏仅限于在明代宫廷表演,亲眼目睹其表演者甚少,相关文献记载只有刘若愚是据亲眼所见载录,其他记载基本辗转源于《酌中志》。据笔者所知,似乎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吴伟业,一个是吴棠桢,他们关于过锦戏的看法源于不同的信息渠道,分别来自于明代宫廷中的其他两个宦官,既可以印证刘若愚之说,又对过锦戏演出规模的辨析大有助益,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吴伟业《琵琶行》序云:“坐客有旧中常侍姚公,避地流落江南,因言先帝在玉熈宫中,梨园子弟奏水嬉、过锦诸戏,内才人于暖阁赍镂金曲柄琵琶,弹清商杂调。自河南寇乱,天颜常惨然不悦,无复有此乐矣。相与哽咽者久之,于是作长句纪其事,凡六百二言,仍命之曰琵琶行”[63]。
吴梅村明确指出其关于过锦的认知源自明朝宫廷中亲眼看过过锦戏表演的宦官姚公(姚在洲),信息源是可靠的。吴伟业既是著名诗人也是戏曲家,曾创作过传奇《秣陵春》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等,对戏曲非常精通。其《琵琶行》中诗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玲珑”直称“过锦戏”“玲珑”,玲珑乃精巧、灵活之意。

《吴梅村诗集笺注》
正因为过锦戏内容简单、体制短小,属于精巧的杂戏,称其“玲珑”十分贴切,如此则过锦戏当属小戏。若过锦戏是百回大戏,吴伟业以“玲珑”评之显属不伦。再看另一个证据。清人宋长白记载:
何次张《宫词》:“昆明池水漾春流,夹岸宫花绕御舟。歌舞三千呈过锦,琵琶一曲唱梁州。”吴雪舫云:“宫中以‘饶戏’为过锦,得之黄开平座上高内相所言”。宫词故实甚多,然历朝各有所尚,五百拣花,三千扫雪,番经奏箓之类。诗人尚未摭拾也[64]。
吴雪舫即吴棠桢,清初戏曲家,《今乐考证》著录其《赤豆军》《美人丹》杂剧两种。金烺《汉宫春·读吴雪舫新制四种传奇》:“小立亭台,见一双么凤,竞啄丹蕉。爱看吴郎乐府,直压吴骚。移宫换羽,却新翻、字句推敲。雄壮处、将军铁板,温柔二八妖娆。 如许锦绣心胸,想琅玕劈纸,翡翠妆毫。自有宝簪低画,红豆轻抛。当筵奏伎,听莺喉、响彻檀槽。若更付、雪儿唱去,座中怕不魂销”[65]。
据此则吴氏至少有四种传奇问世。宋长白明确指出吴雪舫以“饶戏”为过锦的看法来自明朝宦官高内相,当较为可信。既然明朝宫中以饶戏为过锦,则两者的形态应该是相似的,若饶戏是小戏则过锦戏亦为小戏。

《诗词曲语辞汇释》
“饶戏”即“饶头戏”。张相说:“‘饶,犹添也;连也;不足而求增益也。即今所云讨饶头之饶……断送,即赠品之意;所谓饶个某某项者,即饶头戏之意。”[66]。
姜书阁称:“饶就是添,饶戏就是正戏之外,再添演别的节目,那外添的部分便叫饶头。饶头与正项可以是同品种,也可以不是同品种。如买一棵大白菜,又搭一棵葱,即非同种;买一斤橘子,外搭一个小的,则属同种,都叫做饶头。所以在正戏之外,不一定必须加其他说唱、杂技才名饶戏,另演一段小戏也是饶戏。[67]
由此观之,饶戏是与正戏相对而言的,是正戏之外额外添加、赠送的小戏。饶戏表演的位置有三种,一种是在正戏之前,一种是在正戏之中,还有一种是在正戏之后。
饶戏在正戏之前表演的如《张协状元》正戏之前“饶个撺掇末泥色,饶个踏场,……饶个《烛影摇红》断送”是如此,《风月紫云庭》剧:‘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亦如此。
饶戏在正戏之中表演的如《长生殿》演出本,洪昇在《长坐殿例言》中指出:“ 今《长生殿》行世,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吴子愤效《墨憨十四种》,更定二十八折,而以虢国、梅妃别为饶戏两剧,确当不易。且全本得其论文,发予意所涵蕴者实多,分两日演唱殊快。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勿为伧误可耳!”[68]
饶戏表演在正戏之后的情况较多,如明代小说《疗妒缘》中许雄等先点了一本《满床笏》,“未几正本已完,来点饶戏。许雄说一些不知,推与秦仲点。秦仲取戏目一看,说:‘索性做学出来的罢。’就点了《狮吼》一回。又将戏目送入帘内,尤氏就点了《万事足》掷棋盘、《疗妒羹》上团圆”[69]。

《疗妒缘》
此处,《满床笏》是正戏(正本),《狮吼》《万事足》《疗妒羹》中的折子戏均是饶戏。在李渔所作小说《谭楚王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刘绛仙“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都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70]。
这里正戏之后的净丑戏,就是饶戏。明末张岱接待鲁王时,演《卖油郎》传奇,剧完,饶戏十余出,起驾转席[71]。饶戏亦名“找戏”,如明代《梼杌闲评》第四十三回“到了城外,戏子已到,正戏完了,又点找戏。”[72]以此观之,从体制、结构、篇幅、表现内容等来看,饶戏属于小戏之范畴。宦官高内相说明宫中以“饶戏”为过锦,则过锦亦属小戏。
综上所述,过锦戏是明代一种宫廷杂戏的专称,表演以滑稽逗乐、精彩热闹为目的,在继承宋金杂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体现在表演人数增加到十余人,品种更加丰富,有约百回的独立成章的段子,可分可合。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王昊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它由真人扮饰表演,既不是影戏,也不是木偶戏,更没有过锦水嬉或水嬉过锦的品类。其形态是混杂的,不同于单一的杂扮、北杂剧、院本,主要包含了院本和杂耍把戏两大类。就演出规模而言,其形制短小、风格谐谑、情节简单,个体上属于小戏,不同段子合演则属于小戏群。
注释:
[1]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玉熙宫”条(与刘若愚《明宫史》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2]程恩泽《厉宗伯竞渡图为滇生同直题》,《程侍郎遗集》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84页。
[3]翁心存《阳泽门内小马圈是前明玉熙宫遗址》,《知止斋诗集》卷五,清光绪三年(1877)常熟毛文彬刻本,第21页。
[4]秦徵兰《天启宫词》,朱权等《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5]饶智元《明宫杂咏》,《明宫词》,第304页。
[6]参见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一八“过锦”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册,第396页。
[7]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三“皇城一”,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页。
[8]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册,第617页。
[9]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16页。
[10]铁保《梅庵诗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476册,第305页。
[11]参见江玉祥《中国影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5页。按:本文与江先生征引的文献与考辨的角度有所差异。
[12]郝可轩《漫谈皮影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13]高阳《明武宗正德艳闻秘事》,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4]震钧《天咫偶闻》卷七“外城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15]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册,第14474页。
[16]参见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续编》(与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编》合刊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775页。
[17]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8]刘若愚《明宫史》木集“钟鼓司”条,(与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19]李家瑞《傀儡戏小史》,《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4年。
[20]佟晶心《中国傀儡剧考》,《剧学月刊》第3卷第10期,1934年。
[21]孙作云《孙作云文集•美术考古与民俗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22]雷齐明《明清剧种源流谈》,《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按:雷先生引震钧《天咫偶闻》误作李人《天咫偶窗》,其后又云“若据《胜朝彤史拾遗记》的记载,过锦戏‘取时事谐谑,以备规讽’又有些类似唐代的参军戏”。可见,对过锦戏究为何物,颇有犹疑。
[23]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24]周耀明《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25]参见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8页;冯尔康《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26]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1页
[27]《金鳌退食笔记》,第145页。
[28]史梦兰《全史宫词》卷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725页。
[29]荆清珍《明廷禁戏与戏曲刍议》,《长江学术》2008年第3期。
[30]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七“水嬉过锦”条,《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884册,第437页。
[31]高志忠《明代宦官演戏种类考略》,《文化遗产》2011年第3期。
[3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按:王国维先生意识到过锦戏与杂扮的不同,所以他接着又说:“至杂耍把戏,则又兼及百戏,虽在今日,犹与戏剧未尝全无关系也”。
[33]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470页。
[34]董每戡《“滑稽戏”漫谈》,《戏剧艺术》1980年第2期。
[35]参见赵景深、李平、江巨荣《中国戏剧史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页。
[36]吴自牧《梦粱录》卷四“妓乐”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
[37]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27页。
[38]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39]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按:胡先生后来修正了观点,认为过锦是队戏。参见《菊花新曲破:胡忌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页。
[40]廖奔《论中华戏剧的三种历史形态》,《戏剧》1995年第2期。
[41]万斯同《明史》卷四○五“宦官上”,《续修四库全书》,第331册,第385页。
[4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禁中演戏”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8页。
[43]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4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45]李斗著、许建中注评《扬州画舫录》卷一一,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46]佚名《蕉帕记》,章培恒主编《四库家藏六十种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8册,第4页。
[47]《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8—1599页。
[48]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49]章炳麟《新方言·释言》,《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册,第47页。
[50]李玫《明清戏曲中“小戏”和“大戏”概念刍议》,《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
[51]曾永义《论说“小戏”与“大戏”之名义》,刘祯主编《中国戏曲理论的本体与回归》,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52]翦伯赞《清代宫廷戏剧考》,《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53]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7页。
[54]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55]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5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57]张月中、王钢主编《全元曲》(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4页。
[58]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11页。
[59]薛宝琨《相声艺术的源流》,《中国幽默艺术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
[60]洛地《“戏弄”辨类》,《艺术研究》第12辑,1990年。
[61]曾永义《论说“折子戏”》,《戏剧研究》2008年1月创刊号。
[62]李玫《明清小戏的演出格局探源——兼及宋代“小杂剧”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63]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册,第1438页。
[64]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一八“过锦”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700册,第285页。
[65]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册,第8087页。
[66]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27—128页。
[67]姜书阁《说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3页。
[68]洪昇著,康保成校点《长生殿》,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页。
[69]佚名《疗妒缘·听月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70]李渔著,于文藻点校《李笠翁小说十五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71] 张岱《陶庵梦忆》补遗“鲁王”条(与《西湖梦寻》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72]佚名著,金心点校《梼杌闲评》,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