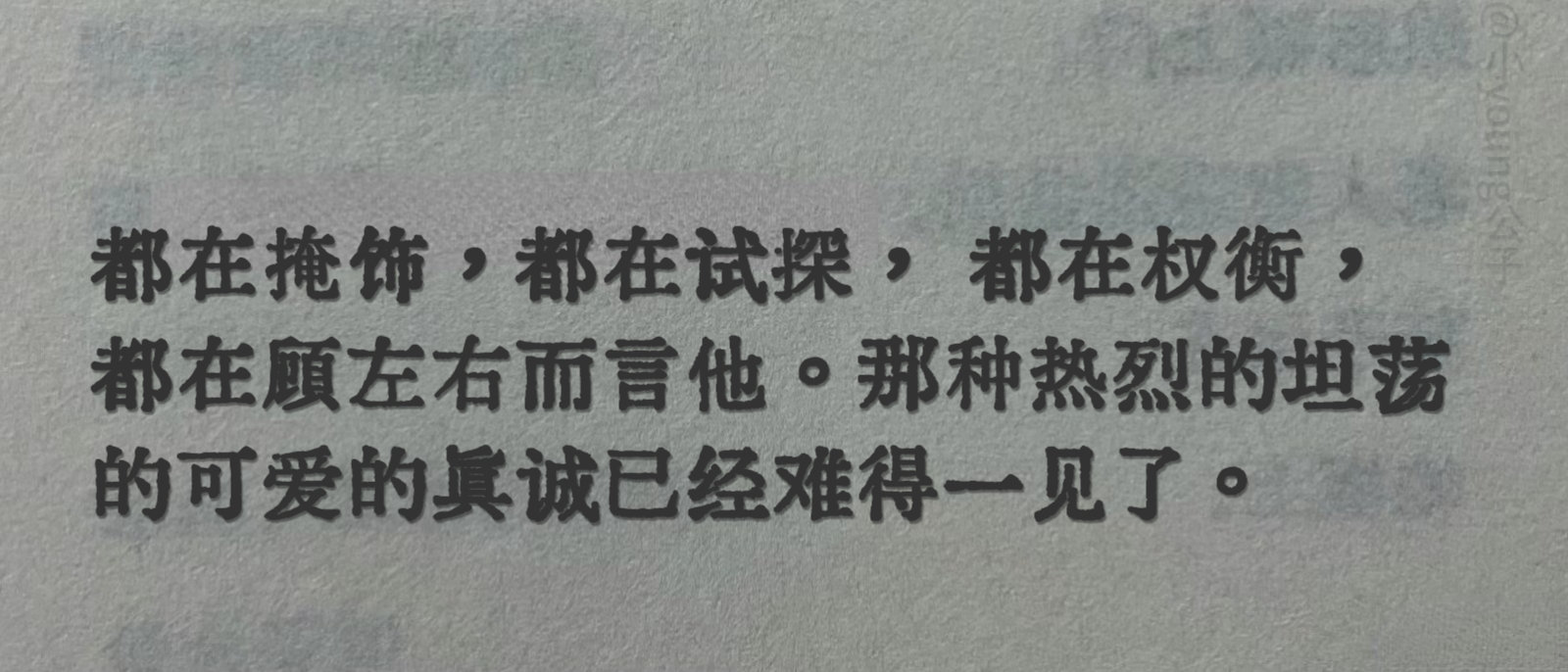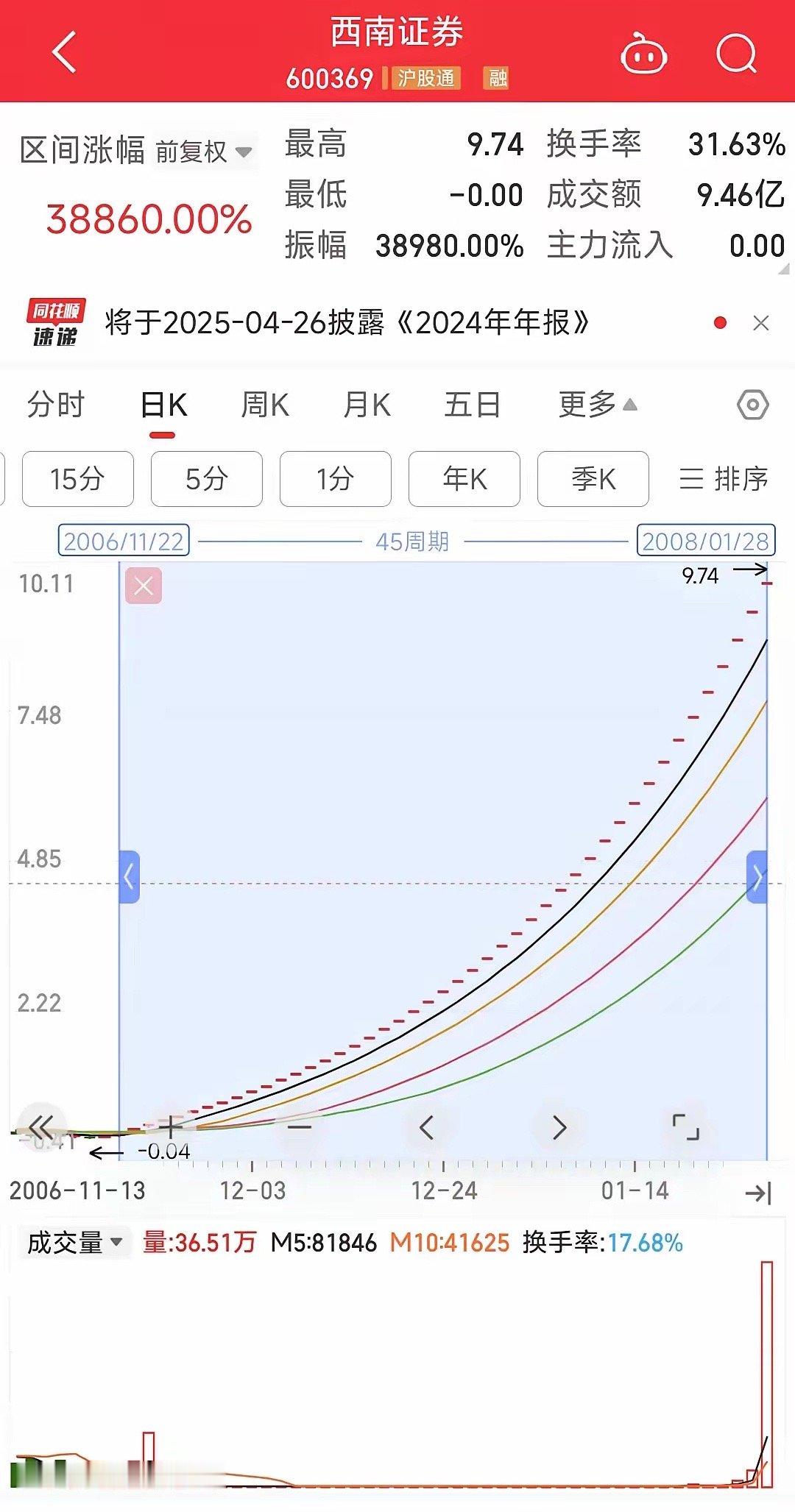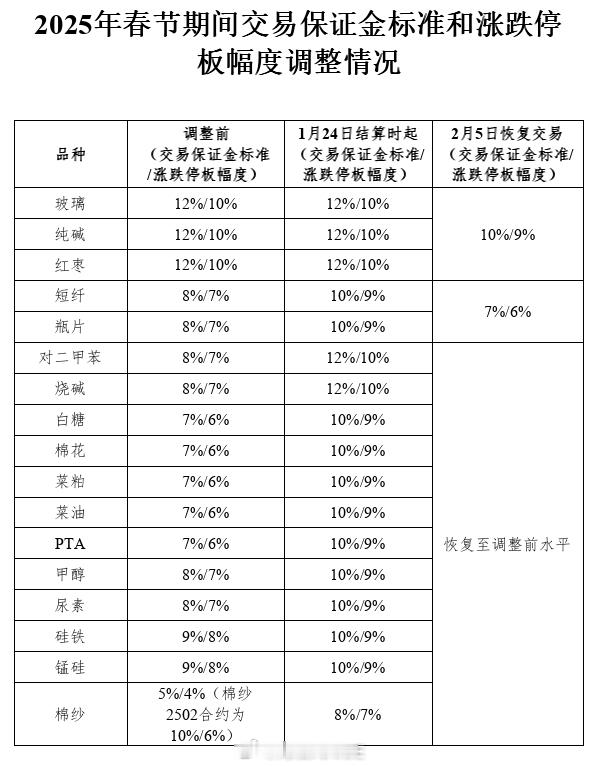政策再定调!争议中的新型储能迎来大转折?
新型储能发展的定位,自从问世的那一天起,从来就不缺少争议,争议一直还非常激烈:诸如“到底要不要强制配储”、“建而不调问题要怎么解决”以及最最核心的——“储能到底能不能”?
然而,随着2025年开年一纸最新文件下达,争议声中的储能迎来一个阶段性大转折。
1月6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简称《实施方案》),掷地有声力挺新型储能。
之所以说“掷地有声”,是因为该文件力挺储能的大背景充满紧迫感:中国新能源装机在逼近14亿千瓦历史关口之后,未来数年每一年都要实现新增装机2亿千瓦以上,且要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不低于90%。既要保装机,又要保消纳,没有一个异常强大的调节资源体系是绝对不行的。
针对目前现实存在的行业痛点,《实施方案》提出了力挺新型储能的几项措施:一是针对配储“建而不调”,强调“优先调度新型储能”以及“应调尽调”;二是强调优化新型储能的充放电价差机制,让它有钱可赚;三是罕见提出“建立市场化容量补偿机制”,这让业内对储能容量电价出台的可能性多了几分乐观。
非常时期的“定调”之下,新型储能已经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争议声中再出发
新能源强制性配储,是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
2017年,青海省发改委印发《2017年度风电开发建设方案》,要求列入规划年度开发的风电项目按照装机规模的10%配套建设储电装置。以该文件的发布为标志,此后数年间尤其是“双碳”目标提出后,先后有20多个省区市效仿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能源强制配储(即业界所说的“大储”)之外,在东部用电负荷中心,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相配套,工商业储能也自下而上自发生长起来。且由于充放电价差机制可以作为投资收益模式,工商业储能一直被业界所看好。
截至2024年底,中国新型储能装机已经突破了7800万千瓦的历史大关;首个储能系统集成商海博思创也在科创板顺利过会。这一切,似乎都在传达着乐观的信号。
然而,即使是政策再定调后重新披挂上阵,新型储能仍要与诸多争议相伴而行。而这一争议,核心指向仍是储能的调节能力。
质疑新型储能的声音,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臻和南方电网专家委员会专职委员郑耀东最具代表性。刘吉臻认为,给电力系统做调节,储能的作用十分有限,就如同“用上几只矿泉水桶来给长江做调节”。而郑耀东则直接对“源网荷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储能与前三者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储能的调节应用到底情况如何?2024年底,官方终于给出了数据:国家能源局在2024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24年1月至8月,全国5800万千瓦的新型储能,累计充放电量约260亿千瓦时。
据此简单约略推算,5800万千瓦的新型储能全年可实现累计充放电量400亿千瓦时左右,如果单独计算储能放电调峰的电量,大概不到200亿千瓦时。
中国近14亿千瓦的风光装机,年发电量大概在1.8万亿千瓦时左右。储能不足200亿千瓦时的调峰电量,之于风光新能源1.8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占比仅仅为百分之一左右。
可见新型储能的调节能力远不是足够的。因而“新起点”之后的发展中,新型储能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调节能力问题。因为抛开征调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等因素,新型储能的调节能力在事实上决定着它的利用率。
在2024年4月举办第12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在主旨演讲中提到“新型储能利用率不高”的难题,并披露,用户侧(主要是工商业)、电网测、新能源强制配储项目平均利用率分别为65%、38%、17%。工商业储能之外,电网测储能和新能源配储利用率都很低。
新政中要求“优先调度新型储能”以及“应调尽调”,未来如何科学调用储能、尤其是在用电高峰时段储能有望发挥作用,对电网企业而言充满挑战。
独立储能收益危机
配储先行之后,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新型储能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独立共享储能,这被业界称之为配储与新能源“解绑”。
2023年8月,山东发布新规,提出功率不低于3万千瓦的新能源配建储能,可按要求转为独立储能。此后,国家电投旗下首个新能源配建储能——吉电股份山东区域公司寿光40兆瓦/80兆瓦时储能项目转为独立储能。
此后,宁夏和河南也出台了类似的配储与新能源“解绑”政策。
两方面原因主导了这一趋势:一方面,随着新能源逐步入市,强制配储的投资成本回收很艰难,配储的能力和动力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允许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有利于让新型储能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电力市场,进而盘活资产,实现储能电站的利用价值最大化。
但独立共享储能也出现了新问题。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在所有储能类型中原本收益占优的独立储能,收益也出现了大滑坡,且下滑势头目前仍在持续。
以储能进入现货市场起步最早的东部某省为例,该省政策允许独立储能通过自调度方式参与现货市场(包括电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获取现货价差收入、容量补偿收入、调频和爬坡辅助服务收入,以及允许储能出租容量获取租赁收入。
尽管在机制上对独立储能百般“呵护”,但是,独立储能在该省还是遭遇了严重亏损。
究其原因,充放电价差缩小的杀伤力很大。
储能在电价“谷段”充电时,相当于午间用电负荷,这抬高了午间电价,其放电则降低峰段电价,储能价差收入则随之降低。在该东部省份,目前独立储能的充放价差已经趋向了0.4元——前期现货价差高时,储能可获得理想收入,而伴随着储能装机多了起来,储能价差收入却随之降低。
实践证明,在增加新能源入市比例的同时拉大现货价格上下限,这些都难以提升储能的价差收入。广东、山西和甘肃等省新能源的大比例入市,都未能提升独立储能的价差收入。
此外,独立储能对容量租赁收入的依赖也很严重。伴随着储能成本的快速下降,独立储能的租赁价格也在持续走低。
还是以上述东部省份为例,储能租赁价格从2023年的240-270元/千瓦/年,已经降至2024年的不足200元/千瓦/年。
并且,因为新能源预期电价持续下滑以及配储比例要求走高等原因,集中式新能源投产规模远低于预期,这也导致对独立储能租赁市场的实际需求严重不足。
而相比之下,更具有充放电价差优势的是工商业储能,江浙地区两充两放甚至可以有1元以上的充放电价差收益,因而工商业储能会持续发展。
未来,配储转为独立储能的趋势在各省市仍将持续,但独立储能收益下滑的问题依然待解。
央、地储能新政有待细化
为了解决新型储能的收益痛点,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推出相关政策措施。
要言不烦,中央此次《实施方案》主要聚焦三大措施:一是强调“优先调度新型储能”“应调尽调”,二是强调优化充放电价差机制,三是提出“建立市场化容量补偿机制”。
三条措施当中,比较棘手的还是储能电站的调用问题。
设想一下,一座县城的晚高峰调峰,调用一两个100万千瓦的煤电厂可能就轻松解决问题了;同等情况下,由于储能电站的“小散乱”,可能需要同时调用几十、几百个储能设施,都不一定能够起到相同的调峰效果。
而站在电网的角度,同时调用几十、几百个储能,操作难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下,“应调尽调”谈何容易?
调用之外,建立储能收益机制也很重要。在这方面,目前上海市已经走在了前头。
据华夏储能此前文章《五年规划定了!上海市将重点发展独立储能,重视收益模式》,1月9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新型储能示范引领创新发展工作方案(2025—2030年)》有两大亮点释放了明确信号,一是明确了储能充放电价格,二是率先提出对储能给予“容量补贴”。
储能充放电价格方面,上海文件规定,迎峰度夏(冬)期间,原则上全容量充放电调用次数不低于210次,充电价格比照煤电基准上网电价下浮50%,放电价格比照煤电基准上网电价上浮20%。
目前,上海的煤电基准上网电价是每度电0.4155元。储能充电电价下浮50%、放电电价上浮20%,一充一放,度电电价价差是接近于0.4元。当然,0.4元电价价差,对于储能全生命周期的收益来说,保障力度还是不够。但是万事开头难,上海总算是在保障储能收益方面迈出了一步,后面根据储能的实践,仍有政策“补刀”的可能和空间。
给予储能容量电价方面,上海文件表述为,对纳入本市年度建设计划,未与新能源项目开发企业达成租赁容量服务协议的独立储能电站,可阶段性给予容量补贴,容量补贴水平将综合独立储能电站充放电次数、参与市场化交易收益等情况明确。
上海是第一个在储能容量电价方面迈出关键一步的地方政府。当然,这一步还不够大。
如果明确要给储能一个容量电价的话,那么有着容量租赁收入的独立储能,也一样应该获得容量电价;此外,储能获得容量电价是基于其在备用调峰方面的作用,因而容量电价也不该眼睛仅仅盯着它赚不赚钱,才去考虑要不要给予它容量电价。
一句话,就像煤电一样,给予储能容量电价是因为它有系统备用的巨大作用。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储能的系统备用和调节能力还不足够,因而全面推出容量电价的时机,还需要不断去积累。
正如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最近演讲中提出的,不断拓展新能源消纳的空间,其重点一个是要靠电网,另一个就是要靠储能。
为新能源提供系统备用和调节,储能准备好了吗?
(转载请标明出处,文章来源:华夏能源网,微信号:hxny3060)
知识百科
- 1 歌讴注音是什么
- 2 被底鸳鸯繁体是什么
- 3 负檐相关词语是什么
- 4 昆明顺丰快递公司具体地址在哪里
- 5 老年退休人员如何网上认证?
- 6 寻戈相关的词语
- 7 趠荦注音是什么
- 8 回暖的诗词 回暖的诗词是什么
- 9 林下风范基础意思
- 10 废务网络意思是什么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