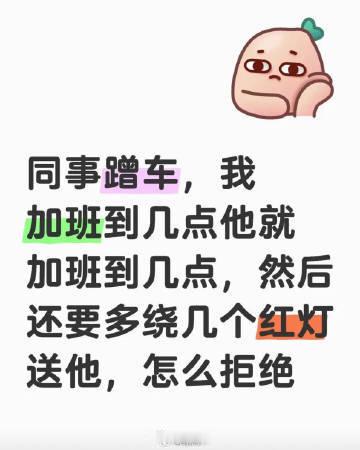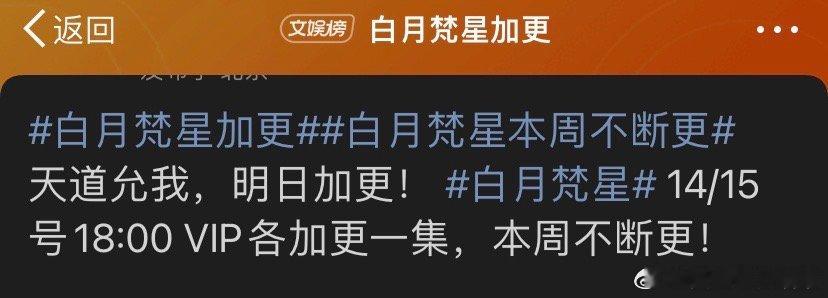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打断了我午后的小憩。是老知青战友王铁柱,一开口就问我还记不记得插队时的淮嫂子。
我一听这话,浑身一激灵,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咱们那会儿要是没帮淮嫂子,她家两个娃娃怕是早就辍学了。"王铁柱在电话那头感慨着。
我闭上眼,1968年的冬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年我18岁,和一群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山西吕梁山区的石峪大队。
记得刚到那天,天寒地冻,北风呜呜地刮着,卷着黄土呛得人直咳嗽。大队长带我们走过几里山路,指着村东头一排破旧的窑洞说:"就住这儿吧,条件简陋,先凑合着。"
窑洞是用山里的黄土打的,墙上裂缝不少,门板都歪了。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
十几个知青挤在三间窑洞里,炕上连个褥子都没有,晚上盖着从北京带来的棉被,还是冷得直哆嗦。半夜里经常能听见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地爬动。
大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个叫淮春花的女人做饭。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瘦瘦的,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两只手总是粗糙通红的,可整个人却透着一股子温柔劲儿。

头几天谁也没往深处想,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在村口遇见她领着两个孩子往公社走。天还没亮透,她肩上搭着块破毛巾,脸上带着疲惫。
大的叫淮根生,七岁,瘦瘦小小的,眼睛倒是大大的,炯炯有神。走路时总是紧紧跟着他娘,像个小大人似的。
小的叫淮小宝,四岁,圆圆的小脸冻得通红。两个孩子穿得都很单薄,大的还好,小的那件棉袄明显是补了又补,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淮嫂子,天这么早,这是去哪啊?"我随口问道。看见她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
"去公社看看能不能贷点钱。"她低着头说,"家里粮食不够吃了,婆婆的药也该抓了。"说这话时,她的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搓着。
后来打听才知道,她男人是两年前在煤窑出事的。那天本来不该他上工,替人顶班去了,结果遇上塌方。留下她带着两个娃,还得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
这事在村里不是秘密,可谁也没想到她家穷到这个地步。我问了问村里人,才知道她家就分了一亩薄地,产量低得可怜,一年到头揭不开锅。
那段日子,我总能看见两个孩子在我们吃饭的窑洞门口转悠。小宝会偷偷往里张望,看见馒头时咽口水的样子让人心疼。

有一次,他趁没人注意,溜进来抓了个馒头就跑。他娘发现后,把孩子打了一顿,还特意送来两个鸡蛋赔罪。那是她好不容易从婆婆的老母鸡下的蛋里匀出来的。
"你们城里人的粮食金贵,可不能糟践。"她红着脸说,手里的鸡蛋递过来时还是温热的。
我看着那两个鸡蛋,心里难受得要命。知道她家连鸡蛋都舍不得吃,全留着给婆婆补身子。
1969年开春后,地里的活多起来,淮嫂子经常天不亮就出工。清晨的露水打湿她的裤腿,午后的太阳晒得她脸颊通红。
有次下暴雨,她在地里干活,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腰。疼得直不起身,还硬撑着把活干完。回家路上,她扶着腰,走一步歇一步,眼里含着泪却始终没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去她家送药,看见小宝发着高烧,躺在炕上直哼唧。根生在灶边煮粥,小手够不着锅台,还踩了个板凳。
淮嫂子连个退烧药都买不起,只能用湿毛巾给孩子擦额头。婆婆躺在炕上直抹眼泪:"春花啊,你就改嫁吧,带着俩娃受这罪,婆婆心里过不去啊!"

"娘,您别说这话。"淮春花跪在炕前,声音哽咽,"死了当家的,我也得把根生和小宝抚养大。您放心,我不会让您饿着的。"
看着这场景,我心里翻江倒海。回到知青窑洞,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着怎么帮她。
正巧那会儿,上面在提倡科技兴农。我灵机一动,找到老支书,说我们知青想在村后的荒坡上搞个"农业科研试验田"。
支书捋着山羊胡子想了半天:"这主意好!能给咱村争光!不过地方得选好,别耽误了集体生产。"
这样,我就带着几个知青,选了离淮嫂子家近的一片荒坡。那地方杂草丛生,石头比土多,蛇虫鼠蚁不少。
我们起早贪黑地干,手上的血泡破了结痂,痂又破。晚上累得躺下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又爬起来干活。
村里人议论纷纷:"这些城里娃,脑子怕是进水了,那鬼地方能种出啥来?""就是,累死累活图啥?还不如多睡会觉。"
可我们谁也没在意这些闲话。就这样干了大半年,硬是把三亩多荒地都整成了台田,还修了条引水渠。每天干完集体活,我们就来这干到天黑。
秋收那天,我偷偷找到淮嫂子:"这试验田是给你家开的。你带着娃来收吧。"她愣在那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那年光景,她家收了七八百斤粮食。年底,她把两个娃送到我教的扫盲班读书。小宝第一次拿到课本,高兴得一晚上都抱着不撒手,在油灯下一遍遍摸着书页。
日子就这样慢慢好转。可天有不测风云,1970年春天,有人向公社举报说我们违规占用集体土地。调查组来了,我差点被打成"资本主义复辟分子"。
关键时刻,老支书和淮嫂子站了出来。支书拍着胸脯说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科研项目。淮嫂子带着全村的贫困户连夜写了份申请,说要把这经验推广到全村。
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反倒让县里觉得是个好典型,还号召其他村学习。后来,整个石峪村的荒坡都改造成了梯田。粮食产量年年上涨,村里人的日子也好过了。
1973年我调到镇上教书,临走那天,淮嫂子带着两个娃来送我。根生已经上初中了,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初中生。小宝也是村里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自家纺的棉线:"自己织的粗布,你带着,到了镇上,记得经常回来看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忍住没落下来。

两个孩子抱着我的腿,怎么也不肯松手。根生说:"叔,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小宝也仰着小脸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像叔叔一样帮助别人。"
日子就这么晃眼过去了五十多年。前年,我专门回石峪村看望淮嫂子。她的大儿子已经在县重点中学当了教导主任,小儿子在省城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盖起了新房子,院子里种满了花。婆婆虽然早已过世,但她每年清明都要带着儿孙去扫墓,还要给死去的丈夫上坟。
"要不是当年你们帮衬,俺们娘几个哪有今天哟!"她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光。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但笑起来还是那么温柔。
我望着院子里那几棵高大的柿子树,是当年我们开荒时特意留下的。树下,她的小孙子正在写作业,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课本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放下电话,我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那些年淮嫂子送的粗布。半个世纪过去,布已经发黄,但依然散发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温暖。
窗外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恍惚间,我又看见了那个在田间劳作的瘦弱身影,和她永远不言放弃的坚韧眼神。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